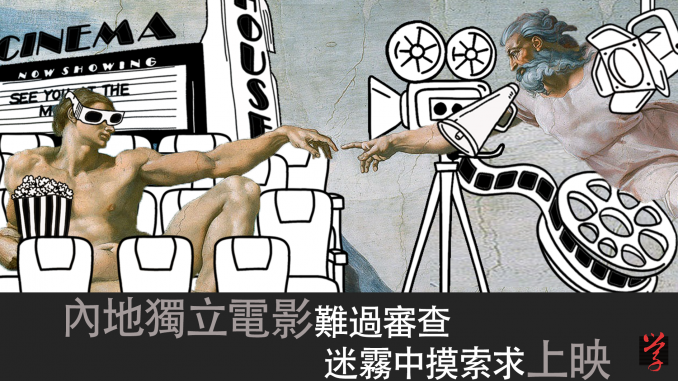
「警察力量過於薄弱」、「不能反映官員貪污腐敗」、「片尾音樂(方言民樂)沒有字幕,擔心有反動言論」……這些看似荒謬的理由,卻確實是內地獨立電影無法通過審查的原因。在不斷收緊的審查制度下,「紅線」無處不在,「創作時把自己閹割一遍,最後送審時又閹割一遍」已成獨立電影人心中默認的準則。模糊不清的審查條例,部門的約談與「拜訪」,都令內地電影人噤若寒蟬,在漫漫送審路上舉步維艱。
記者|王梓萌 編輯|張凱元
在山東長大,自幼迷上中外電影的獨立製片人水某(化名),在台灣銘傳大學畢業後回到北京追尋電影夢。在電影公司工作的三年裡,他發現到行內人僅在乎電影的收益,而他更着重電影能否傳遞思想,於是毅然辭去電影公司製片人一職,自立門戶。
在內地,電影上映前要交到電影局審查,通過審查、獲得「龍標」(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才可在院線、串流平台上映和參與電影節。若私下將未通過審查的電影放映,製作團隊可能會面臨最高過百萬的罰款,甚至是牢獄之災。

電影含犯罪情節僅評0.9分 「正能量」結局亦未過審
「獨立」的身份雖為水某帶來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時迎接他的是崎嶇不平的審查路。兩年前,他參與的一部電影便因未能通過審查而無緣上映。該電影講述一個身患絕症的兄長,為了給有志成為音樂家的弟弟籌錢舉辦音樂會,不惜與朋友鋌而走險,走上犯罪路的故事。水某和拍攝團隊自知故事「不太正能量」,故特意安排警察成功將犯罪分子捉拿歸案的結局,為求讓電影更正面,能通過審查。
這種自我審查的例子在內地電影業十分常見,水某直言「審查是刻在腦子裡的,我們甚至做夢都在想到如何通過審查」。然而,即使結局如此「正能量」,水某的電影終究無法過審。在以10分為滿分的電影審查意見表中,該片僅獲0.9分。電影局在「存在問題及修改意見」一欄中表示,故事「展示了主人公扭曲的人生觀、醜惡的個性和以觸犯法律來達到目的的價值抉擇」,即使有正面的結局亦無補於事。電影中的「警方遲遲不採取行動」,亦被批評「對警察等正義力量的描寫過於薄弱,與法治社會現實嚴重背離」。
按照規定,未通過審查的電影可以根據電影局提出的意見修改,並二次送審,但水某認為所謂的修改意見實際是一種「勸退」:「難道我們要把整個故事改成一個愛情故事嗎?沒法改,除非重拍」。送審的電影花了一年時間拍攝,耗資100萬元,製作團隊聯同演員合共上百人,資金是靠他行內的前輩幫忙牽線,找到幾間肯投資的公司而得來的,但水某表示這次的失敗令「他們(公司)沒有信心再去投資了」,「放棄它,是一個對我們所有人都好的結果」。而且即使重拍,電影仍需再次提交電影局接受審查,水某感歎:「這道題你不會,你寫十遍也不會」。
「不想自取其辱」 拒將作品送審
面對審查這道「不會寫的題」,有人乾脆擱筆,另闢蹊徑,尋找上映以外接觸觀眾的途徑。
曾獲「鳳凰網行動者聯盟」評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的紀錄片導演蔣能傑,2010年起花近十年時間記錄家鄉湖南省邵陽市的村民,為了生計上山採礦而染上塵肺病的故事,製作出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馬夫」是負責趕馬運送物資的人)。然而,擁有逾十年電影從業經驗的他意識到,鄉村貧困話題是審查制度下不可觸碰的「紅線」,「我們現在全面脫貧了,怎麼還會有貧困問題呢?」。
帶著「不想自取其辱」的想法,蔣能傑並未將影片送審,在2019年12月完成《礦民、馬夫、塵肺病》後,他選擇日夜守在內地影音平台「豆瓣」的網頁上,以私信方式向每一位點擊「想看」的用戶傳送其雲端(網盤)連結。據「豆瓣」資料顯示,至今共有7.7萬人表示「想看」這部紀錄片,為該片寫下觀後感的更有過萬人。百度網盤官方亦一度在微博上為影片宣傳,表示「歡迎更多獨立電影人和創作者來網盤首發」。


三度被約談 未送審電影終消失
儘管並未送審,《礦民、馬夫、塵肺病》仍難逃「被審查」的命運,蔣能傑三次接到不同部門的致電和約談。
最先「找上門」的是蔣能傑公司註冊地——廣州的公安部門。當時,蔣能傑正在網上發起眾籌活動,為《礦民、馬夫、塵肺病》籌集製作資金,但由於未有申請拍攝許可,隸屬廣州公安部門的「文化執法大隊」隨即要求他「刪掉」眾籌活動的宣傳,並退回籌得的五、六萬元人民幣。其後,當地文化體育局再約見他,對談的一小時裡,對方多番質疑他的拍攝目的,「拍這些是想幹甚麼?」、「(你的電影)不符合電影法,還會違背憲法」;又警告他「不要(把這部影片)做出來」。
最後蔣能傑沒有屈服,被「約談」後三個月,電影完成拍攝,他卻一直處於擔驚受怕的狀態,「(影片)就是非法出版物,我擔心他會不會來抓我」。終於在一年多以後,蔣能傑被第三次「約談」。這次向他發出「邀請」的是公安部政治安全保衛局,指他在網上「上映」未獲過審的紀錄片,要求他將相關連結刪除。
自此,內地的觀眾再難以看到《礦民、馬夫、塵肺病》。百度網盤官方也刪除了該段宣傳,如今若再點開蔣能傑分享的連結,畫面只會白底黑字地顯示「百度積極響應政府『淨網』行動號召,打擊網上隱晦色情信息」。
「紅線」邊界模糊 戴著腳鐐難跳出優美舞蹈
然而,蔣能傑亦非全然放棄正規的上映途徑,抱着 「玩一把」的心態,他把新片《矮婆》送審。這一次他成功了,這套講述一個留守女童在種種經歷後離鄉尋找雙親的電影終於2021年上映。將《矮婆》送審的過程,蔣能傑形容是兩度「閹割」,「我這個片子要過審查,所以創作時把自己閹割一遍,最後送審時又閹割一遍」。電影中,貧困兒童到工廠工作的鏡頭被要求刪減,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童工」;「官員收禮」的鏡頭須改成官員堅拒不收,因為「不能反映官員貪污腐敗」;片尾的當地民樂被要求加上字幕,因為那是方言,他們聽不懂,擔心是甚麼反動的歌詞。
面對種種無理刪減、更改的要求,蔣能傑無力反抗,「不改他就不給你龍標,不給你發許可證,他們現在就是這麼流氓」。他表示,這些被要求刪減的內容,並沒有訂明在《電影產業促進法》內,從業者只能自行揣摩,以及與「同行取經」來判斷「紅線」的邊界。這樣的試探,蔣能傑形容是「帶著腳鐐跳舞」,反問「能跳出優美的舞蹈嗎?」
送審如石沉大海 知名導演亦「求審無門」
不只是獨立導演,中國「第五代」電影代表人物,曾獲多項國際電影大獎的導演田壯壯,在8月發布的影片《田壯壯:我和電影的關係》中表示,其執導的《鳥語嚶嚶》拍攝完畢後送審至今已有兩年,至今仍未曾收到任何回覆。該電影講述一名農民與知青鬥爭的故事。他提到,他願意接受任何審查結果,卻無法接受「我送給你兩年多,你連一句話都沒跟我說的結果」,又坦言這次經歷令他再一次對電影失望。

疫情、審查雙重打擊 獨立電影人唯有另謀生計
無法通過審查,意味著電影無法上映,創作者投放的時間、金錢通通都化為泡影。對於沒有公司依附、沒有穩定投資方的獨立電影人來說,被扼住咽喉的不止是作品,還有自己的生計。水某無奈地表示,擔任獨立製片人的三年裡工作「沒有收支平衡,一分錢沒賺。所有都是我們在支出,沒有收入」。為了拍攝《矮婆》,蔣能傑亦動用了原本為買房子而存下的40萬元。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亦殃及電影業,水某歎指電影是一個隨時被拋棄的產業,「沒有太多(投資者)願意去投資電影了」。
為維持生活,獨立電影從業者不得不將目光轉向他處。水某將工作重心放在經營電影社交媒體賬號上,他寫影評、電影上映資訊等的微博帳號有逾200萬粉絲。給其他電影寫一篇五星好評,可為他賺來800到6000元不等的收入。拍攝廣告也是他另一個收入來源,他曾為意大利一個奢侈品品牌拍攝抖音廣告,五段影片能賺得15萬人民幣,「我其實不太喜歡拍廣告,但它是一個很賺錢的行業」。蔣能傑亦透過拍廣告賺取收入,其他電影作品參與比賽獲得的獎金也是重要收入來源。
在「紅線」下的掙扎困難重重,但水某與蔣能傑都表示,將會在獨立電影之路上繼續堅持下去。水某堅定的道:「中國有非常棒的獨立電影工作者。他們用影像書寫歷史,書寫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我們堅定了創作的決心和態度的時候,審查制度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