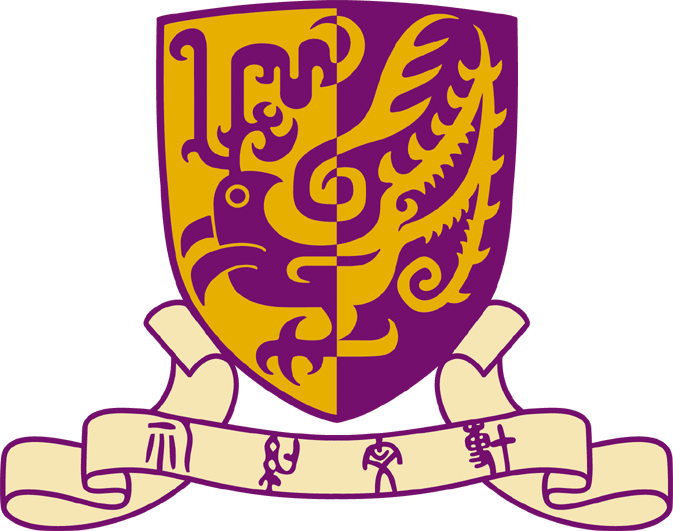1 April 2022
“Seeing the world in worm’s eye view”: In dialogue with soundpocket founder Yang Yeung
Anthropologists tend to observe the nuance and details of thing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wider culture and society we live in. In this episode, we invite art writer and curator Yang Yeung to share how anthropological training equips her with unique sensibility and a “worm’s eye view” to see the world. Yang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then pursued MA in Anthropology at Yale University and PhD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has worked as a journalist and documentary director, and founded the non-profit soundpocket in 2008 to promote sound and listening as a form of art and culture. She is currently teaching at the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at CUHK.
(This episode is conducted in Cantonese.)
01’26 Anthropology as a way of observing people
15’51 Cross-discipline ‘clash’
20’35 Anthropological way of viewing art
35’24 Being tiny but powerful
[Podcast excerpt, available in Chinese only]
楊:楊陽 ANT: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ANT:我想好多人以藝評人或策展人的身份認識你,比較少人知道你曾讀過人類學碩士,可否請你分享一下你是如何開始接觸人類學呢 ?
楊:我在「石器時代」時在香港大學就讀社會科學本科,當時香港大學沒有人類學系,但有位老師叫 Grant Evans,他是當時系內唯一一個人類學家,我完全不知道人類學是什麼,但他教的課堂好好玩,我曾經做過一個去廟街的考察,做過另外一個較長的考察是去殯儀館了解他們的工作。我發現去接觸和觀察人,以及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自己生活的環境,是十分吸引和開眼界的事。
ANT:你本科畢業後工作了三年就到耶魯就讀人類學的碩士,當時為何有此決定?
楊:我記得我上課時 Grant 講過一個說話:race is an invention,我幾十年來都記在腦內,一直都有回去反思他的意思,多年後的今天仍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甚至到今天仍然 prevalent,即很多人仍覺得種族是一個可靠的將人分類的方法,但人類學的角度就絕對不是這樣。
我現時在大學通識基礎課程任教,當中有「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在後者我們有講到達爾文的進化論,也講到某一個時期有人會強用咗這套理論去講 Social Darwinism 和 eugenics, 在這些討論上,先前所學過的概念就會回來,如權力,以及人的認知上的固執,但同時對科學有種迷思,或將科學扭曲偽科學,這些都跟以前的 exposure 有關。另外一句我很記得老師講過的是 “to be near enough is not good enough”,我當時不太明白他的意思,那時我比較關心的是自己學術上的追求,譬如為何選擇去耶魯等,但這句話在生命上面也很適用,在我喜歡做的事情和藝術當中,要去認識一個人真的不能只是 come near,而是要把任何一個人當成一個全人去相處,同時別以為你可以完全了解他的一切,實在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拿捏中間的距離,並且知道自己處於什麼位置與人建立關係。
我曾經在電台做紀錄片導演,我們做的紀錄片都沒有 narrator 去講故事,而是用畫面和人物自己的說話去講故事,當時差不多廿四小時 on call。擔任那工作時,我不會無端想起學術那種人類學,但我相信有些營養是來自人類學的。當我拍紀錄片時,我很珍惜與人建立的關係,同時意識到有責任把那些東西呈現出來,並從一個 emic 而非 etic的角度出發,意指我們不需要再外加一把間尺作批判,而純粹以受訪者本身的話語和世界觀講故事。手持攝錄機的時候,某程度上我們都形成一個權力關係,我們要學習如何把自己縮到好細好細,但不可以消失,那種敏感度很大部分來自人類學。對我而言,人類學是一種生活方式以及接觸人的方法。
ANT:後來你於中文大學修讀文化研究博士,你認為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三者之間有何關連和異同?
楊:我想我自己一直在朝向的方向,正正是尋找不同事物或學科之間的橋樑以及相通之處,不同學科之間的界線其實已經畫下了,我曾經歷過這些界線,但我自己其實不太跟那些界線走。我修讀 Intercultural Studies PhD 時,那一科在中大還是很新的,讀PhD 的過程大家都明白是超級孤獨,因為你的題目可能只得你一個人在做,你可以討論的對象只有supervisor,我當時選的題目是關於 cyborg 和 humanism,簡單而言就是人到底處於什麼情境,而我寫論文時,已經沒有考慮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關係,也未有理會我在邊一個學科當中,為哪一個 system of knowledge 去付出,我純粹覺得「人點先為之係人」這問題不可以輕易放過,如Donna Haraway 在 ”A Cyborg Manifesto” 講到在 techno culture 當中的挑戰是如何理解我們的主體性,或者在一個簡單稱作 science-dominated 的當代文化之中,我們如何自處,這些問題對我們而言十分重要。我當時的 supervisor 是哲學人,那時我開始感覺到不同學科之間的 clash,那些碰撞有它的歷史原因,但有時候我覺得是不必要的,不同領域之間其實可以多啲傾計,去發掘更多可能性。
ANT:你的教學和學術背景橫跨不同學科和領域,你認為人類學在當中有何獨特的位置?它如何影響你往後的工作和生命?
楊:我已經忘了是哪位老師說過,應該都是Grant,他說人類學是用蟲仔的眼睛,而非birds‘ eye view去看世界。這對藝術寫作以及了解藝術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用一些宏大的架構去分析或解釋事情的因果關係,很多人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些工作很重要,但我不擅長。而在藝術的 interpretation 當中,description 與 explanation 同樣重要,很多時候要找一個 causal explanation 是很困難的。現在我看藝術作品時會着眼於作品的細節,可能要看很多次或者花很長時間,不停問自己問題:我看到什麼?藝術家可能想表達什麼?
我最近為一個立陶宛攝影師的回顧展寫文章,我花了半年時間去看他的作品,我把自己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可能想表達的東西都寫在文中。我會說我們跟專業的人類學家做考察仍存在很大的距離,但我亦覺得不是人人都要跟從那一種人類學的方式去做。我最近在 youtube 聽一個人類學家說好多人欣賞人類學家做田野或者看世界的方法,他們會有自己的方法去做人類學,而這是值得 celebrate 的,我認為這種多元也很人類學,他們不是憑自己的知識建立 authority,而是很慷慨和謙卑地分享所知的事,而這種態度對於我做人很有幫助。
ANT:我很好奇你剛才講到人類學如何幫助你觀看藝術作品這點很有趣,我知道你除了寫藝評外,亦創辦了名為 soundpocket 「聲音掏腰包」的聲音藝術組織,可否請你分享多一點人類學和藝術的關係?
楊:人類學和藝術我立即想起一個日本藝術家下道基行,他曾在大館跟香港藝術家鄧國騫舉行雙個展。下道基行曾說他小時候想讀人類學,但最後選擇了藝術。他當時的作品名為《十四歲與世界與邊界》,在日本、台灣、香港、韓國找來一些十四歲的中學生,跟他們進行工作坊,訪問他們覺得生活中有什麼邊界,並請他們想像如何回應那些邊界。之後他把他們的故事寫成故仔,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展覽一部分展出了這些新聞剪報。
他亦曾在沖繩的海灘執拾玻璃碎片,再找當地的工匠將之溶掉整成新樽,他想研究當地美軍的 military history 與當地居民的關係,亦對 local craftmanship 感興趣,那些新製的玻璃樽因質地不同而有裂痕,這很有意思,重整原來可能引致裂痕,但重整的過程中,他得以接觸欣賞的人,對 material culture 和歷史有新的認識。現時他在直島的一個已停用的社區中心,放置當地居民收集的關於當地旅行的書,像個小圖書館供大家閱讀,又會辦放映會。他是一個做作品很成熟的藝術家,但他覺得接觸人,以及講他們的故事,比起自己不停去做作品更加有意思。
現在想來,人類學確實有些很細微的敏感度,以及不會容易接受社會既定的 hierachy,總是去問問題,思考如何重整這些 hierachy。我又記得以前上 medical anthropology 的課,第一堂老師叫我們想想自己的 hierarchy of healing,當自己或者身邊人遇到病痛時,會首先去看醫生還是做些什麼?我覺得好有意思,因為他肯定了每個人對生命的自主性。
ANT:無論是人類學,還是聲音藝術,在香港都屬較小眾的領域,你認為這些東西對香港社會有什麼重要性?
楊:先講「聲音掏腰包」吧,我會形容我們是藝術界的微生物,在藝術界很多人都會講「生態」,這生態中要有大、中、細,不同的 institution,我認同這是必要的,但我們「聲音掏腰包」會將自己看成微生物,微生物好多都是對環境有益的,它可以消化或者拆解污染物或者其他東西,只有好少部分對人有害,但以 biodiversity 或者生態的角度,微生物是有需要存在的,所以我們都喜歡保持微細,這跟剛才所說的用蟲蟲的視角看事情也有關係。
我認為我們做的所有事都構成文化的一部分,而所有事情都有人文的面向,那不是 reduction,而是一種看事情、世界和自己的角度。如果以這個角度去想,其實每一個範籌都不需要放過,亦不需要比較,我有時候覺得這些從某個角度而言是細而無力的東西,可能更有力量,when the time comes,它發揮的作用可能更大,尤其是當它們不是平時高調宣揚自己,大聲主張一些 statement 或者去插旗的時候,那種 ambiguity可能會帶來更多驚喜和機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