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素的《自傳》序言中,這位哲人提到他一生追求的兩樣東西:「我極期渴望能夠洞悉人心之所思……我竭力參透數字主宰萬物變化背後的玄機。」
籠統而言,人文學者竭力了解人心;科學家則致力尋求永恆不變的自然定律。認知科學家則介乎兩者之間,他們最想破解人類認知及推理的神秘法則。教育心理學系李雅言教授,透過瘋魔全球的「數獨」遊戲,可能已找到每個人都有演繹推理能力的證據。
演繹法是一種推理過程,在前提是真實的情況下,其結論必然真實。後天論者認為一般人至少要受過相關訓練,始可演繹推理。但李教授的研究,正正提出相反的事實。
當李教授仍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時,他就留意到英國《泰晤士報》連載的「數獨」遊戲廣受大眾歡迎,從八歲小孩到八十歲長者,不論何種教育程度或社會階層均愛不釋手。
「數獨」據說是由十八世紀的偉大數學家萊昂哈德.歐拉的拉丁方陣衍生出來。典型的「數獨」是一個九乘九的矩陣,每個矩陣內又有九個三乘三的小矩陣。矩陣部分方格內有數字,部分留白。玩法是在每一列、每一行及每一小矩陣的空格內填上1至9的數字,但在每列、每行和每個小矩陣內,1至9的數字每個只可出現一次。
李教授認為,雖然這個遊戲是找出從缺的數字,但「數獨」本身不涉及任何數理或運算步驟。光是運用推理,便足以解開「數獨」的謎底。李教授進一步假設,沒有受過訓練的人,也可透過簡單策略去完成任務。簡單策略就是從已知的確切數字,推斷出從缺的數字。舉例來說,若1至8各個數字已出現於一列中,那麼餘下的數字必然是9。一連串的簡單策略漸漸發展成為步驟,讓玩的人可以偵破難題。
明顯地,「數獨」的難易程度視乎規限條件多少,或所謂關係複雜度而定。若從缺的數字需要同時通過行和列對數字的規限,那就得花上更多時間和精力去解難。在這個例子之中,行與列便是規限條件,關係複雜度是2。最後,對於那些較難的遊戲來說,簡單策略可能不管用,故要使出進階策略。這些進階策略有兩個步驟:個人首先推測某些空格中的可能數字,接着利用這些可能數字去淘汰其他空格中的可能數字。在每一個步驟中,個人仍需要倚靠簡單策略。
為了測試這些假設,李教授等學者在一個實驗中邀請先前沒有接觸過「數獨」的中大學生,試玩三種不同難度的「數獨」(圖一至三)。他們要在十五分鐘內,盡量填上缺少的數字,也要解釋為何會作出這樣的判斷。研究發現這些首次接觸「數獨」的學生,在十五分鐘內就能自發地掌握一些推理策略。正如實驗者所預測,大部分學生採用了簡單策略,而從他們提出的理由,足證他們意識並可清楚地解釋選擇這些策略的原因。
在第二個實驗中,一批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獲邀試玩一系列關係複雜度由2至5的「數獨」。結果發現「數獨」難度愈高,解難策略也相應加深,學生需要發展出進階策略,要紀錄下有可能出現在空格中的數字。換句話說,簡單策略只能夠應付簡單的遊戲,不足以應付更艱深的遊戲。
在最後一個實驗中,二十名中大學生分為兩組進行進階策略的測試。第一組學生的遊戲跟第二個實驗的相似,但部分空格提供了可能出現的數字(圖四);第二組學生則沒有。換句話說,第一組學生不用採取進階策略的第一個步驟,可以馬上用已有的提示去剔除那些可能性不高的答案。正如所料,第一組學生可以更快捷、更容易去解開「數獨」難題。
李教授等研究者總結,「總的來說,『數獨』遊戲可以證明沒有邏輯訓練的人也有能力去就抽象事物作出推斷,他們也樂於作這類推斷。」* 這結論質疑那些認為演繹邏輯能力是需要透過教育和經驗得來的心理學理論。
這項研究的另一個發現,是部分學生遇上較難的「數獨」時會調整策略,令我們對人類的思考過程甚至創意思維了解多一點。事實上,李教授把他的個人研究興趣與他培育年輕學子的熱忱結合起來。身為伍宜孫書院輔導長,他透過簡單卻能挑戰思考的遊戲來鼓勵學生思考他們是如何思考的,並分析當中的過程,從而發展出創意的解難方案。以他任教的「思維心理學及其應用」課程為例,藉着跟學生玩珠機妙算,探討不同假設測試策略的效用。莫可測向的人類心靈活動,將會繼續是李教授的研究焦點。
* N.Y. Louis Lee, Geoffrey P. Goodwin & P.N. Johnson-Laird (2008): The psychological puzzle of Sudoku, Thinking & Reasoning, 14:4, 342–364, at 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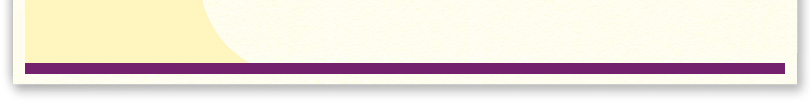





























































































































































社交網路書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