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讀者: 《中大通訊》已停刊,本網暫停更新。請移玉步造訪本校最新通訊《走進中大》網頁:https://focus.cuhk.edu.hk,閱讀大學報道和消息。
探索廣東話的誤區
張洪年暢談粵語現象,解開數個迷思。

張洪年教授,中文大學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榮休教授,祖籍江蘇鎮江。稚年來港的他,自稱「外江佬」,熱愛語言,尤其是粵語。他在4月上旬應新亞書院第二十九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之邀回港,為觀眾帶來三場精彩的粵語及文學講座。《通訊》特請他從語言學的宏觀角度,暢談粵語的一些現象,並澄清一些誤區。
我們現在詬病的懶音,日後會演化為正音嗎?
語言發生變化,今音不同古音,這是一個十分自然的現象。今日粵語常常把音節前面的[ŋ-]鼻音丟失,好像把我[ŋɔ5]讀成[ɔ5],一般人會認為這就是所謂的懶音。「我」古代屬於疑聲母,是一個舌根鼻音,今音保存古代[ŋ-]的讀法。不過古代屬於疑聲母的還有其他的字。就以「疑」字本身為例,古讀[ŋ-],今卻讀[ji4],顯然已經把舌根鼻音丟失。但是為甚麼我們不說這是懶音?原因很簡單,日久已成習慣。「疑」字丟失鼻聲音總有百多年以上的歷史,今日粵語已經沒有[ŋ-]的讀法,但是「我」字丟失[ŋ-],卻是這幾十年才比較流行。對還保鼻音讀法的人來說,這種沒有鼻音的讀法聽起來顯得奇怪,以為是一種為了發音省力而產生的壞習慣。不過現在年輕的一代,把[ŋ-]丟失的人越來越多,假以時日,我們可以想見「我、疑」都可能一律不帶鼻音聲母,到了那個年代,今日所謂的懶音會成為新的標準發音。
我們可以再舉一些別的例子說明語音變化的現象。例如粵語中常把[n-]讀作[l-],例如「你」讀作「李」,這也是常說的粵語懶音現象之一。不過,有些方言如四川話,也有[n-]和[l-]不分的現象。但是四川話卻把[l-]讀成[n-],恰恰和粵語的現象相反。如果說[n-]發音困難,於是偷懶讀成[l-],那麽爲何四川人倒反過來把[l-]變成[n-]?難道是四川人認為[l-]比[n-]難發音?說粵語的年輕人也常把韻母部分的舌根韻尾[-ŋ]讀成舌尖韻尾[-n],例如剛本是[-ŋ]、乾是[-n],發音各異,但現在剛乾不分,都讀成[-n],許多人以為這是因為[-ŋ]發音比[-n]複雜,所以就偷懶說成[-n]。但是我們知道南方的國語常把韻尾[-n]讀作[-ŋ],例如「民」、「名」,本是[min2][miŋ2]之分,但南方國語、台灣國語不分,把[-n]也讀作[-ŋ],這變化的方向卻正和粵語相反,那又怎樣用偷懶來解釋這現象?用懶音來解釋語音的變化只是一種印象式的描述,並不可作準。
語音的演變是否由民眾說了算?是不可擋的嗎?
硬要把語音定於一尊,是可以的。但是由誰來決定?根據甚麽來決定?定於一尊的目的到底又是甚麽?這就富於爭議。自民國以來,便把國語/普通話定為國家語言,標準發音都以北京話為基礎。但是我們知道北京話和標準漢語的發音並不完全一樣。例如「誰」的標準音是[shui2],北京人大多說[shei2]。今天要是一個北京人參加朗誦比賽,把「誰」讀成[shei2],也許評判先生會會認為不夠標準,評分的時候會打折扣。
標準不標準往往是一個主觀的判斷。如果一百個人當中,九十九個人都保持一種老派發音,只有一個人獨持新派發音,那當然是多數人佔優勢,認為新派發音不可接受。政府或法定的語言委員會也許可以規定這老派發音是標準音,所有正式場合必須跟隨。這種人為的努力或能把自然的語音變化拖慢一點,但是刻意的外在糾正和自然的內部變化在相互角力之下,最終誰會勝出?我們從語音史可以看到許多例證。尤其在今天的社會上,人們普遍不容易接受建制強加的標準,壓力愈大,反動力量也愈大。
其實說到底,語言最大的規範能力就是約定俗成。等到九十九個人都說新派的發音,那個獨持原先老派標準的發音的人,就成了異類。有人問我是否贊成懶音。作為一個研究語言的人,我的工作是如實描述語言的現況和變化,我不會也不應該帶有任何價值判斷的眼光來指三道四。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假如我有孩子,我希望他說哪一種語言,都是標準的發音。上海話這些年來變話很大,我能說一些上海話,但是我的發音跟新派的很不一樣。我不會用懶音來描述上海話的變化,但是在直覺上,我還是覺得老派的比較好聽。這也許是老人的一種戀舊的情懷使然。
那你也覺得今不如昔嗎?
如何定義「昔」?五十年代?還是二十世紀十九世紀的才算夠標準?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常覺得BBC英語發音才是標準,美國人的英文就不夠典雅。但從語言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的英文本來就是從英國搬借過去,許多地方都保持了伊麗莎白年代的語音特色。而現在的所謂英國口音其實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今不如昔,那麼嚴格的說,美式英文的發音應該比英式英文更為老派,更為經典。但是為甚麼有很多香港人會覺得英式英文好聽,這背後的原因,很值得我們去探討。
戀舊是感性的,但如果作為一種自我肯定,藉此以批評別人口音難聽,那便是價值判斷和態度取向。人人都有口音,要說中國的政治領袖,打從孫中山先生數下來,有哪位政治家的國語是標準的?毛澤東、蔣介石、馬英九、習近平,說話都帶口音。我們中國人說英文略多略少都帶有中國口音,如果我們說英語遭受批評,我們會覺得是一種冒犯嗎?我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說英語的人,英文是我後學的語言,有口音自然是意料中事。美國人不講究英國式的BBC英語,但是美式英語,又以哪種為標準?紐約的?波士頓的?美西的?美國南方的?各地有各地的方言。現在有所謂的Englishes,也就是說英文已經不再定於一尊,各國有各國的英語,各地都有其方言,除英美以外,還有愛爾蘭、蘇格蘭、加拿大、澳洲、南非、新加坡等等英語,各種英語,平起平坐,各有自己的身份,都值得語言學家深入研究。
在新亞書院唸書的年代,我們並不那麽執着於口音。老師沒幾位說標準的國語。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等等講課,各有自己的鄉音,學生聽課有時候感到很吃力。但是我們從沒有討論老師的發音標準不標準。當年我們讀書的時候只會注意一個人的一手字是否寫得好看,所謂字為衣冠之美,發音好與不好,對我們來說意義並不重大。現在的年輕人,說話似乎比寫字更為重要,這也許是時代變了,價值觀也有所改變。
粵語保留了最多的古音,朗讀詩詞歌賦最能保持原有聲韻之美,是嗎?
粵語歷史悠久,這話一點不錯,但是哪種語言沒有悠久的歷史?福建話中就保留了一些秦漢時代的語音。「茶」字潮州話的發音近似「爹」,聲母讀[t],這是上古音;廣州人讀「查」,是後起的發音。張和鄭這兩個姓,閩語讀[t-],也是上古的發音。所以保存古音的不只是粵語而已。
大家最常提到的是粵語完整地保存了[-p][-t][-k]三種入聲韻尾、和[-m][-n][-ŋ]鼻音韻尾這些特點。今天的北方話,入聲韻尾[-p][-t][-k]確實是已經消失,[-m]韻尾也合併到[-n]。但是保留入聲的不只是粵語,也有方言是保留[-m]韻尾。另一方面,現代粵語也丟失很多古音,例如古代齒音有三套,現在的粵語卻只有一套,但是普通話仍保了三套—也就是現代拼音中的j/q/x:zh/ch/sh:z/c/s。其實一百年前的粵語還有兩套齒音,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才歸攏為一套。總而言之,粵語確實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語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失去了很多。
用粵語朗誦古詩詞的確悅耳,例如《滿江紅》中的「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又如《聲聲慢》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這些詩詞以入聲押韻,用粵語朗讀,特別能帶出其鏗鏘效果。不過試讀《長恨歌》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國、得、識三字,今日粵語發音完全不一樣,讀來就不覺得是押韻。但是在古代確實是屬於同一韻,只是韻母後來各自演變,到了今天的粵語,雖然都屬於[-k]韻尾的入聲韻,但是元音各不相同,古代押韻的效果在今日粵語中就完全感覺不到。可用我的母語鎮江話來唸,起碼「得」和「識」仍是押韻的。那麽,說粵語保留古音,當然不錯,但是不能就此認為粵語是存古,或者是最能保留古音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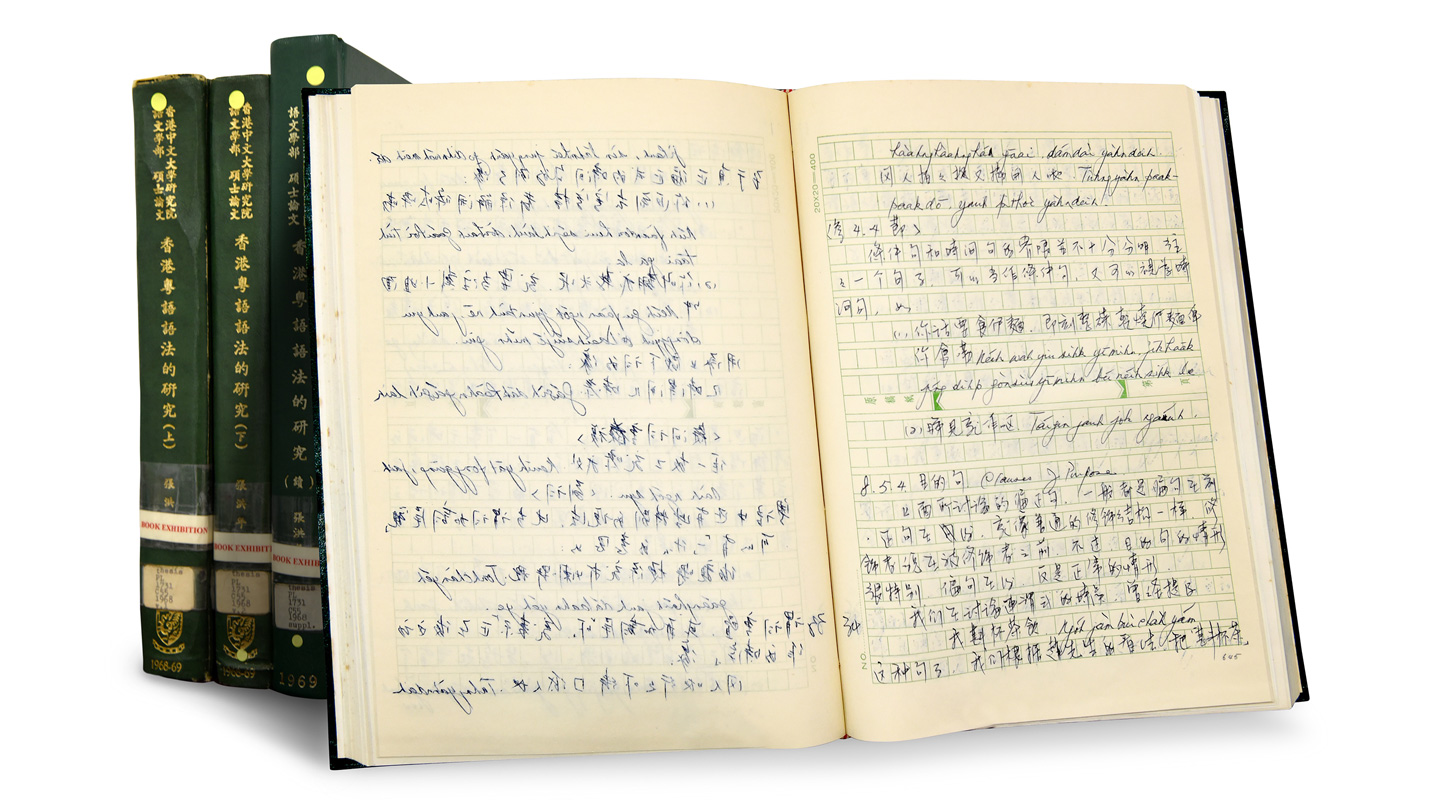
粵語生動傳神,是其他語言所不及的,對嗎?
不同語言各有其生動之處。我們熟悉自己的語言,所以最能體會到和掌握到自己母語中的微妙情趣。我能說相當流利和標準的國語,但是我和北京人交談,聽相聲段子,在節骨眼上,卻不一定能完全明白。這就是因爲他們的話語中夾雜了很多方言俚語,我不是在北京生長,對當地的風俗和習慣了解不深,於是許多話中有話的地方,都無法明白或參詳。我們說廣東話歇後語精采,我體會很深,每每看到或聽到老的或新編的歇後語,都會噱然。但是我也深信甚麽方言都有自己的歇後語,各有巧妙,雋永之處並不遜色於粵語。
普通話是否比廣東話文雅?
文雅的定義是甚麼?南蠻之音,佶屈聱牙,我們都知道這是一種偏見。我年輕的時候曾經非常着迷法文,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可是有一次在法國一小酒店裏住宿,一大早被吱吱喳喳的聲音吵醒,窗外傳來兩個法國女人吵架的聲音。哦,法文原來也可以這樣難聽。我剛學日文的時候,覺得日文過於咬牙切齒,頓挫繁雜。後來有一天我在教授的辦公室裏聽到他和別人打電話,語氣溫文,舒緩有致,我這才知道日文是這麼美的一種語言—可惜我怎麼也沒學會日文。
用普通話學習中文,寫作無須經過口語轉化為書面語的過程,會寫得更好嗎?
不一定。這裏面的前設是現代的白話文是以北方話或普通話為基礎,所以書寫的時候,只要把口語轉化為書面語,就會文從字順,四平八穩。沒錯,會說普通話的人寫作時確實是少了一層先在腦子裏把自己想說的話怎麼從方言翻成普通話的轉換過程。不過就是因為這樣,能說普通話的人都能寫好的文章嗎?北京人成千上萬,一口京片子,人人都可當作家了?當然不。寫作不就是我手寫我口那麽簡單。寫作是另外一種深層次的訓練。文章要寫得漂亮,得靠先下苦工,多讀書,多看古典文學,從中汲取養分,以補不足。古人所謂熟讀唐詩,不會吟也會偷,那就是根基功夫。就像烹飪,難為無米之炊。肚裏沒有墨水,能寫得出甚麼?香港以前中小學的中文教學,選取古今範文,教導學生,從最基本功入手。那個年代栽培出來的學人,國語不一定說得漂亮,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如何看「普教中」、「棄繁從簡」等爭議?
語文政策如果涉及政治因素,我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否則,我們應該用持平的態度來看問題,千萬別感情用事。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首先是教學應該用普通話還是廣東話?其次是漢字書寫應該採用簡體字還是繁體字?其實這兩個問題都得先問我們為甚麼要在兩者之中選其一?選擇的目的又是甚麽?繁簡之別自古就有,書寫的時候,為方便起見,常常會省減筆畫。中國近代推出簡體字和漢字拉丁化方案,主要目的卻是在於掃盲。掃盲這個需要在現在香港的社會中還仍然迫切嗎?既然沒有這個危機或需要,那麼我們教學為甚麼不就從繁體字開始?繁體字歷史悠久,一兩千年的古代典籍,今天還能一個字一個字讀得出來,那是多麼可貴的資源。要是教學全然以簡代繁,文化承傳也許會出現危機。不過中國大陸推行簡體字好幾十年,所有出版基本上都是以簡體字為主。我們要是不認識簡體字,那也會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純粹從學習漢字的角度來看,是先繁後簡、還是先簡後繁容易?答案應該很清楚。在外國教漢語往往是要求學生對繁簡兩體都能掌握,以便他們日後能廣泛使用各種不同的中文資料。
另一方面,普通話是國家語言,我們不能不學習。我們都知道只要一踏出香港,能用上廣東話的場合就很少。所以從實用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趁早學習普通話。小孩越早學習外語,越能掌握對這個語言的語感。但是學習普通話並不是說要用普通話來取代廣東話。香港絕大部分的人的母語都粵語,香港以母語教學,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不能因為普通話是國家語言,就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這就像中國不會因為英文是世界語言,就把英語硬性定為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廣東話和普通話為甚麼不可以共存?我們熱愛自己的語言,但是也不必抗拒別的語言。今天許多年輕人都感到政府的決策好像處處在掣肘或打壓粵語的發展,於是產生一種無以形容的語言憂慮感,因為憂慮,所以多方推崇粵語,過分的推崇,會形成一種語言的優越感,從而造成對其他強勢語言的抗拒。從憂慮到優越,主要是導源於外在社會或政治的誘因。我們假若不從根本層面來正視、解決這個問題,這問題恐怕會變得越為複雜。
研究語言給你最大的滿足感是甚麼?
語言並不如想象中那樣古板或死板。相反地,語言是一種有機體,他有自己有蓬勃的生命力,而且不斷在變化。乍看起來,語言似乎是一堆雜亂無章的聲音和字詞。其實在這亂七八糟的背後,大有脈絡可尋的組織和變化。我們研究語言首先就要觀察語言是怎麼通過聲音來表達意思,從聲音字詞的組合,整理其間的關係,歸納出組合的規律,解釋變化的模式。這些變化可能只屬於說話者個人的習慣,也可能是方言之間的異同,更可能是古今語言變化的痕跡。我們甚至可以根據這種規律和模式,從而預測語言日後發展的路向。語言不斷在變,我們就不斷的在捕捉、描述、解釋這種變化。我們個人對這些變化的喜惡取捨,無關重要,我們最大的責任就在於能把握和利用這些變化來提高或增進我們對這語言的了解。這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但仔細研究下來,我們會發現人的思維常常是共通的,而表達思想的各種語言形式和變化也有很多類似的特點。我們要是不從最細微的素材做起,就難以窺其大觀。這樣看來,語言研究可以是一種跨時空的探討,挑戰性越強,我們就越感到興奮。
本文縮略本見《中大通訊》第4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