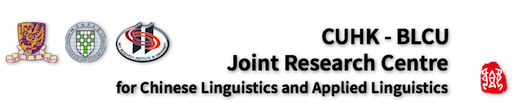二月文化沙龍精彩內容
日期: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
題目:錢穆的院士之路及其與胡適之交涉
主講人:翟志成 教授
本次沙龍在城市大學樂聚坊舉行,主講人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原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翟志成先生,題目是「錢穆的院士之路及其與胡適之交涉」。翟先生綜合運用檔案、未刊書信、日記、回憶錄等史料,採文本分析之進路,重尋錢穆先生入選院士之曲折歷程,由此引出對近現代學術思想史演變的整體反思。中央研究院於1948年選出第一屆81位院士,其後隨國府遷臺,院士中留陸者多達59位,在臺灣及海外者22位,不足三分之一,院士會議實際陷入癱瘓。1950年代,胡適希望以「院士」光環吸引、團結海外學人,故提出以登記人數為實有全體人數的解畫方案,使得院士評議會恢復運轉。1958年,中研院新選出第二屆院士14人,其中人文學者有蔣碩傑、姚從吾、勞榦4位,而學術成就及影響皆在四人之上的錢穆先生反未能當選,實可怪也。同年12月14日,嚴耕望致書胡適,建議在次年第三屆院士選舉中當「延攬錢賓四先生」,以爲此舉不但出於錢穆本身之史學成就,更可釋外界對錢、胡隔閡之疑,正「漢高封功自雍齒始之義」也。胡適隨即發動提名錢穆之活動,12月29日致書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云錢氏提名表已得姚從吾、董作賓、勞榦及自己簽名,尚缺一位方足五位提名人之數,邀請朱氏加入。胡適未邀請其他人文院士(多在美國)為錢穆提名,轉而求諸數理組的朱家驊,蓋因朱氏近在臺灣,如此方能趕上提名之截止日期,同時擁有朱氏提名,也有利於獲得數理科學院士之投票。由此,錢穆進入中研院院士提名,接下來便是初選投票。當時投票者七人:胡適、趙元任、王世傑、董作賓、李濟、姚從吾、勞榦;除了胡、董、姚、勞四位,李濟後來也簽字擔任錢穆之主提名人,按常理這五位都應當支持自己提名的對象,而趙、王二位皆是胡適好友,也應配合胡適的延攬計劃——可見胡適在前期的提名安排頗費苦心,看來錢穆獲選當無疑問。但投票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錢穆得票竟然僅有一票!這不但遠遠少於以七票通過的楊聯陞,更説明提名錢氏之人也紛紛「跑票」,方才出現如此尷尬的局面。那麽,這僅有的一票出於誰人?翟先生推斷,此票當是胡適本人所投,因延攬錢穆乃其既定策略,若胡適不欲錢穆獲選,沒有必要大費周章地為之奔走安排。院士評議會上的「跑票」事件,正説明當時中研院學人對錢穆學術路數的質疑:胡適、傅斯年等倡導考據為治學之正道,非此則不視爲學問,錢先生雖然以其《先秦諸子繫年》一度被胡適視爲考據上的同道人,但以《國史大綱》為代表的通史之學卻不獲胡、傅一系學者認可,割席抗禮,也是意料中事。
此後第四、五、六屆院士人文組增選了陳槃、周法高、何炳棣等先生,但錢穆之名,卻遲遲不見諸榜上。直至1968年,錢穆方被選為第七屆中研院院士,提名人是第六屆院士何炳棣。何先生曾回憶云是他説服了院長王世傑,促成錢穆當選,但實際之情形遠非如此簡單。原來,推動此事的決定性力量,乃是「老總統」蔣中正。在文化立場上,蔣與錢可謂真正是「氣味相投」,新亞書院早期也曾接受臺北總統府的資助,由蔣向王世傑施壓,增選錢穆為院士,可以說是合理的解釋。而近年出版的許倬云回憶錄中,更直言「後來老總統介入了,他要王雪公非把錢先生選出來不可」,正是一條直接的證據。實際上,錢穆當時與中研院史語所仍頗有芥蒂,李濟便托辭拒絕出席新任院士的就職典禮,以示抗議;錢穆也僅僅出席了當選的酒會,後來再不踏入南港一步,大概彼此都有點「羞與絳、灌同列」的味道吧。倘不是顧及蔣公的面子,錢穆很可能連酒會也未必出席!
錢穆這一遲來的「院士」頭銜,平生不願齒及,相形之下,反倒是對港大、耶魯的榮譽博士更津津樂道,其中不無深意。更可嘆者,不論錢先生本人抑或當時學界,一直以來也多指胡適為「阻撓」錢穆院士之路的「罪魁」。事實上,如前所述,胡適不但在嚴耕望的勸説下推動了增選錢穆之事,還投下了當時唯一的一張支持票。但嚴耕望出於避嫌,曾請胡適不要透露他獻議之事,而胡也頗有君子之風地信守諾言,使得這段曲折鮮爲人知。不過,胡適對錢穆的支持,乃是出於延攬學人的策略需求,他内心對錢氏之學並不認同。在現代中國所面臨的中西衝突之中,胡適主張治沉疴當用猛藥,故批判中國文化多有過激之論,實際上是矯枉過正、策略性的「西化」,並不相信中國文化會消亡。在此立場下,胡適與高談中國文化傳統之學人,自然頗不同調,不但視錢穆、張其昀等為「未出國門的苦學者」,即馮友蘭,也被譏以「雖曾出國,實無所見」。北大歷史系曾有解雇蒙文通之風波,官方的説辭是蒙氏講課有口音,但實際之原因恐怕還在於蒙文通治學走義理一路,不見賞於胡、傅等人。與此類似,胡適對錢穆通史一路的學問,也大不以爲然,傅斯年至有「平生不看錢穆書一字」之語,可見一斑。反過來,錢穆對胡適經過了仰視、平視再到俯視的發展階段,在文化立場上,錢先生主張,主人在家方能接引賓客,故欲吸收西洋文明,中國之本位,決不可廢。錢、胡之分歧,牽涉到學術理路上的考據、義理之別,更關乎傳統文化在現代的定位;在其當時,胡適一方是學界的主流,掌握主要的話語權,但就長時段的學術發展來看,錢先生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輩如今成爲了中研院執史學牛耳之人,胡適、傅斯年一派則反倒影響日微,此消彼長,頗堪玩味。在學術發展的歷史上,考據並非永遠是主流,甚或「主流」與「邊緣」也大可以互為轉化。
錢穆崎嶇的院士之路,在學術史上祇是一件小小公案。錢先生之學問成就,煌煌俱在,院士之頭銜,絲毫不能損益之。不過,學術史之大關節、大脈絡,由此正可窺見。本次講座引發了在座諸先生的熱烈討論。張隆溪先生贊同翟先生的看法,認爲錢穆與胡適代表了對中國文化基本看法的兩種不同思路;但也提出胡適思想或許也經歷變化,並非一直激進。馮勝利先生提出胡適與乾嘉學術的關係問題,認爲「西化」的胡適在學術研究上採用傳統的考據辦法,很可注意。陳致先生則指出胡適的考證中也不乏邏輯錯誤與想象的成分。翟先生回應云,胡適本人固有多面性,其待人接物甚至比一些新儒家學者更爲「儒家」;他認同乾嘉考據,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胡適在傳統「考據」中讀出了「科學精神」其二則是他希望通過「考據」則是要揭露「寳相莊嚴」背後實際上「不過如此」,以「考據」為舊文化「驗屍」。胡適雖以《中國哲學史大綱》大得聲稱於世,但他的興趣實不在形而上學,他所理解的實證主義,主要也是一種輕淺的實證主義。關於錢穆獲選院士的細節,大家也很感興趣。朱慶之先生提出應尋找更多證據支持「胡適投票」之說;翟先生表示唯一贊成票出自胡適乃是自己的推理,目前沒有直接的文獻證明,但從當時的情勢看,此乃最爲合理的推斷。張隆溪先生又提問,何炳棣向來不喜新儒家,何以提名錢穆?華瑋先生也提出,既然錢穆之增選出於總統府,何炳棣何以自居提名之功?翟先生進一步解釋了這些疑問,何氏的觀點是見人之長而非論人之短,他看重《國史大綱》的成就,因此力主增選錢穆為院士;何先生對總統府之介入未能悉知,因此認爲是自己説動了王世傑,也非無因。同時,「新儒家」的範圍,也有廣狹之分,余英時先生便否認錢先生為新儒家。狹義言之,倘以熊十力系統作界分,則徐復觀先生亦非「新儒家」;廣義言之,以新亞書院和《民主評論》為其論學陣地,則錢穆先生是當仁不讓的「新儒家」。張宏生先生由中研院與整個中國學術界的關係,聯想到1940年代中央大學與學界之關係,以學衡派為中心的東南學者,與中研院就頗爲疏遠;但他們在當時的學術界也很有影響,教育部「部聘教授」文學科唯一一位就是中央大學的胡小石。張健先生指出,與中研院關係接近是北大一系學人,兩派路數頗不相同,背後正有新舊之爭。李歐梵先生注意到李濟不喜錢穆的問題,認爲考證、考古佔據主流,使得解釋一路的學術,包括文學闡釋以及對儒家思想的解釋,都受壓抑;胡適對文學實際上未必有很深的瞭解,他是一個登高一呼的人物,好處在能開創新風氣。劉笑敢先生由錢穆的遭遇聯想到當下學術界評價體制的很多問題,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輕的錢穆,當年的遺憾是否會重演?《亞洲周刊》主編邱立本先生也從此次講座引申到當代思想界古今中西之爭的很多問題。翟先生最後用楊萬里的詩結束講座,寄予他對錢、胡二位乃至整個近現代學術史的省思: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待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