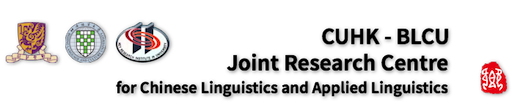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 講者: 馮勝利教授

2015年第六次「午間雅聚」──古代詩歌節律與四六文的韻律機制
2015年11月30日,中國文化研究所「午間雅聚」活動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馮勝利教授擔任講者,與我們分享其最近的研究成果,演講主題為「古代的詩歌節律與四六文的韻律機制」。
馮勝利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馮教授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語言學系,於美國堪薩斯大學及哈佛大學任教語言和文化十五年。2010年加入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要研究方向為訓詁學、歷史句法學、韻律句法學和韻律詩體學。出版學術著作有《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漢語韻律句法學》、《漢語韻律語法研究》、《漢語韻律詩體學論稿》、The Prosodic Syntax of Chinese等等;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馮勝利教授首先說明,作為語言學研究者,他將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詩歌和駢文。馮教授指出,西方語言學無可否認對現代語言學研究產生很大影響,但接受了中國語言文學系培養的學者,往往更關注中國語言與文學本身的一些獨特問題。在中國詩歌史上,最早出現的是二言詩。問題是為什麼四言詩發展起來以後,二言詩便消失了?為什麼先有四言詩(《詩經》)而後有三言詩(《郊祀歌》)?為什麼三言詩之後才有五言詩?為什麼五言詩產生後,三言詩反倒衰落了?五言詩以後為什麼沒有六言詩?六言體運用最廣的為什麼是漢賦和駢文?從語言學角度,言即字,字即音節。何以中國詩歌的音節呈現上述發展進程?馮教授認為,這是中國幾千年詩歌發展中值得去探討和研究的問題。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一個開端或解釋。
馮教授先從詩歌誦讀的問題談起。他以「鋤禾日當午」這首五言詩為例,五言詩似乎可以誦讀為三拍(鋤禾#日當#午),也可以誦讀為兩拍(鋤禾#日當|午)。七言詩似乎亦可誦讀為三拍(一片|飛花#減卻|春)或四拍(一片#飛花#減卻#春)。從語言學的角度,兩種誦讀方法體現了兩種節律結構。「一片#飛花#減卻#春」是「二二二一」的節律結構,「一片|飛花#減卻|春」的讀法則變成了四三的兩節結構。
馮教授接著討論哪一種誦讀方法更加符合古人的語感。五言詩是漢代末期出現,七言詩則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盛行於唐朝。清朝皇族後裔,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啓功先生曾記錄中國詩歌的節律和吟誦方法。根據《啓功全集·第一卷》的記錄:四言詩應誦讀為兩節,六言文如「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一樣誦讀為兩節,每一節的開頭一個字不算拍。第一節開頭的字為節外拍(即英文所稱extrametricality/anacrusis),第二節的頭一個字為「間拍」(拍與拍之間的襯字)。還有,七言句「爽籟發 而 清風生」讀作兩拍,中間的「而」字不算拍。而另一首七言句「落霞 與 孤鶩 齊飛」讀作三拍,中間的「與」字同樣不算拍。這樣的誦讀規律告訴我們,字數不能作為劃分節拍的根據,詩歌的虛字常不算拍。有些不算拍的字為半起拍(如「帝高陽之苗裔兮」中的「帝」(即節外拍)。詩歌有自身的節律法。唐朝和尚遍照金剛在《文鏡秘府》中也談到詩歌的節律「兩句律」(句即停頓,節律單位):「上二字為一句,下一字為一句:三言;上二字為一句,下二字為一句:四言;上二字為一句,下三字為一句:五言;上四字為一句,下三字為一句:七言」。遍照金剛認為,中國詩歌的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是誦讀為一行兩句,都是兩節。詩行以一行兩節(句)為佳。這是遍照金剛的詩歌語感,也反映出當時人們誦讀詩歌的節律法。這一節律法被後來當代著名學者及詩人林庚稱為「半逗律」,即前後各一節∕一行兩節、兩個韻律單位:「將詩行劃分為相對均衡的上下兩個半段,從而在半行上,形成一個類似『逗』的節奏點」;「『半逗律』與不同的『節奏音組』(即『大音步』,比標準音節兩音節音步大的三音節音步)的配合,構成長度不同的典型詩行,而且『節奏音組』總是落在行尾位置上,它決定了詩行的特殊性」。(《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大音步總是落在詩歌行尾,這是詩行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的原因,至今仍是還未解決的問題。
對於中國詩歌節律的規律,馮教授進行了一些研究併發現詩行遵從自然音步,即誦讀時從左到右,兩字組成標準音步,最後奇數的字總是與前面的音步一起,形成一個三個音節的大音步。在音步組成以後,節律基本呈現三種規律,齊整律,懸差律及長短律,由此形成一個節律功能的完整體系。不同的節律形式表現不同的語用功能和風格,如齊正律表現的是雅正風格,而懸差律則有俗諧的效果,這便是節律的語體意義。例如,懸差的節律常被運用於一種諧體詩—三句半,造成一種強烈的諧趣風格。
馮教授根據從以上規律總結中國詩歌的一些特徵。根據「半逗律」,詩行最低限度一行要兩個音步(韻律單位),因此,沒有一言詩,最起碼是二言詩。但是二言詩按照前面所提到的節律規則沒辦法誦讀,這暗示中國語言的節律規則在某個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也推翻了四言詩是由二言詩發展而來的簡單結論,因為兩者的節律規則並不相同。漢學家葛瑞漢(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就曾提出漢語曾在西周前後在節律類型上發生過重大變化,而二言詩正是產生在西周以前。
另外,詩歌與說話不同,詩歌有音樂性,有旋律,而旋律的本質在重復。因此,詩歌的根本因素在其音樂性和重復性,這是詩歌語言的形式特徵。詩歌的基本旋律便是齊正,提煉口語的節律而形成的整齊有序的話語形式,體現有規律的重復,呈現詩歌的節拍、押韻、平仄等。長短律則是根據口語中的自然節律而提煉成的話語形式,形成一種散文體的風格。懸差律則是根據語言輕重形式提煉而成的俗諧節律,更多的運用於諧俗體,造成諧趣效果。
馮教授在此基礎上繼續分析四六駢文。他指出駢文是詩和文的組合體,駢文不是散文,而是介乎散文與詩歌的語言形式之間。四六文為什麼不是四六詩?因為「詩律及文律具根本上的不同:詩律要求詩句以兩個韻律單位復迭組成,六言詩標準韻律有悖於此;文律則容許句內輕重、長短不一,使六言句內變化多端」(盧冠忠,2013)。
馮教授從節律角度總結漢語詩歌結構的最小條件(Minimality Condition)是單音不成步,單步不成行,單行不成詩。因此,詩歌最小的音步 = 兩個音節(two syllables),最小的詩行 = 兩個音步(two feet),最小的詩段 = 兩個詩行(two lines or a couplet),最小的詩節 = 兩個詩聯(a stanza, quatrain or 絕句)。這是漢語詩歌的基本節律結構。從這個角度看六言文,在誦讀的時候,若是兩字兩字形成三個音步,則不符合詩歌的「半逗律」,若是按照二四或者四二分節律,則節律懸差太大,不符合詩歌的齊整律,因此六言的詩感與五言、七言並不一樣。由此可以解釋六言詩歌並沒有在中國廣泛流傳的原因,因為六言形成的詩感並不強,而賦有很強的以長短律為基礎的詞感。從節律角度還可以解釋詩歌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許多其他現象,也為馮教授在講座最初提出的幾個問題提供一個解答的切入點。
文章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