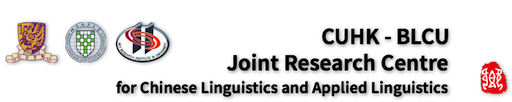漢學講座(二):「東亞藝術史研究在歐洲的源流和發展」
5月15日10時30分至12時30分,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JRCCLAL)通過Zoom舉辦了「2021漢學講座」第二講。本系列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張健教授與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統籌並主持,特邀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參與策劃。本次講座講題爲「東亞藝術史研究在歐洲的源流和發展」,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羅泰教授主講,張隆溪教授擔任對談嘉賓。
張健教授:
尊敬的羅泰教授,尊敬的張隆溪教授,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健。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舉辦系列的漢學講座,邀請世界各地著名的漢學家介紹漢學的傳統、現狀、未來,以及他們的研究成果。今天是系列講座的第二講,我們特別榮幸邀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爲我們主講,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擔任對談嘉賓。
羅教授是傑出的考古學與藝術史學者,研究成就卓著,他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並曾經獲得美國考古學會的最佳圖書獎。羅教授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對談嘉賓張隆溪教授是傑出的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學者。張教授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對於西方現代文論的研究曾經影響幾代學人,他的《道與邏各斯》等專著也有重大的影響。張教授是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的外籍院士,他曾經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主席。
今天非常巧的是主講嘉賓羅教授與對談嘉賓張教授是哈佛大學的同學,所以今天是一次非常特別的聚會,我們相信今天的講座與對談一定異常精彩。我們也安排了提問環節,歡迎各位在線的朋友加入討論。我簡短的介紹就到這裡。現在有請羅教授開始。
羅泰教授:
謝謝張教授。今天非常榮幸跟大家在屏幕上見面,並且很高興給大家介紹一些學科歷史的事情。我覺得東亞美術史的歷史,可以當作一個新的學科被學術體系包容的典範,我以後會再慢慢解釋這一點。所以我今天講的不僅僅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例子,就是給大家舉例,如何能夠讓一個學術領域進入學術界——我不敢說進入學術界的主流,這個時間可能還沒有到,但是至少可以進入。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奇怪的事情,我早就意識到,也許大家對此也有體會。大家都知道國際上凡是有一點名氣的大學,都有各種東亞的語文課程,甚至會有這方面的學系。文學被廣泛介紹到國際學術界裡面,基本上所有的名校都有這樣的課程。
可是,東方美術史,也就是說中國、日本、韓國,還有東南亞國家的這些美術史,相對而言,在這些國際名校中的課程和教員比語文少得多;但是也能夠在比較好的學校找到,至少歐洲每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國家,學術傳統比較深厚一點的國家,現在都有這方面的教授。
還有音樂,東方音樂好像目前在學術界的代表是最少的,極少有學校能夠專門學到東方音樂。儘管大家都說音樂是一種共同語言,不需要任何翻譯,大家都能夠直接明白,但是其實歐美人在研究中國的古代文明時,覺得最難理解的卻是音樂。他們理解得最少的是音樂,其次是藝術,理解得比較多的,還應該算是文學和哲學之類的。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個現象,但是我現在就要開始向大家介紹一下,東方美術史研究是怎樣進入西方的學術界。我們從歌德(Goethe)開始講,歌德看起來不太看重東方的視覺藝術,不但是中國的,還有印度的和埃及的,他覺得好是好,但是不重要,不會對我們在道德和美學上的教育提供任何幫助。
這個態度當然非常奇怪,因爲歌德親自翻譯過中國詩,他並不是看不起中國文化,他知道中國這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可是他就沒有看到過中國比較高級的藝術,他看到的都是裝飾藝術。當時18、19世紀初,歐洲人能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裝飾藝術,以瓷器爲主,還有另外一些工藝品。現在我們認爲應該作爲美術史研究對象的中國繪畫、書法,還有佛教美術,他都沒有看到。也許這樣就能夠解釋,並且明白歌德的偏見。
歌德這一代的人已經看出來,研究人類的文化傳統不能局限於歐洲這個地域。他已經把他們的視角開闊至全世界包括中亞,當然他們的訊息並不是很全面,但是他們對這些東西至少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這方面的工夫,在19世紀初期以來的德國建立的大學系統裡比較明顯,而且這裡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Wilhelm von Humboldt(洪堡特),他是建立柏林大學的一個語文學家。他把Philology(文獻學、語文學),把學語言定爲研究人文科學最基本的任務,以達到德語verstehen(理解)一詞所指的狀態,即是能夠進入異國文明的這麼一種思考方式。然後就在這個基礎之上,把原來比較狹窄的文化觀,(原則上可以)擴展到全世界。
Wilhelm von Humboldt還有一個弟弟,叫做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一個地理學家。他曾經到新大陸做過好幾年的科學調查,然後回到歐洲寫了大量的著作。他也是這麼一個態度,他強調人類的同一性,否認了不同種族的人之間的任何不同,認爲精神文化屬於全人類,沒有任何高低差別。
Alexander von Humboldt進一步解釋,從我們現在或者他們當時的客觀狀態來看,當然有一些族群也許還沒有完全在發展水平上一致,還有一些不平等,但是全人類都有本能可以達到最高的文化水平。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idealism,德國的「理想主義」的思想狀態。
Wilhelm von Humboldt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他非常大膽地認爲人類歷史總會往一個互相理解的狀態來發展,會逐漸地消除各種各樣的偏見,會消除不同民族、宗教等等傳統的人爲區別,而且這背後有歷史的必然性。在Wilhelm von Humboldt的視野中,他想像中的大學應該在促進這方面的發展上起作用。
在這種背景之下,就發展出我們現在還能夠看到的歐洲大學傳統,尤其是在人文科學裡面:基本上以語言規定學術專業之間的分界線,建立各自的學系。讓專家先學他們的語言,然後根據這些知識來研究這方面的文化傳統,視覺藝術是後來跟這個拼湊到一起的。
視覺藝術真正被學術界注意,好像並不是在德國,而是在法國;也不是在19世紀初期,而是在19世紀大概50年代以後。在當時有日本潮流,Japonisme,(歐洲)從日本引進了一大批工藝品。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量出口手工質量很高的藝術品,引起了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比較大的注意,也引起了模倣。在這種狀況之下,才第一次出現了有關東方美術的專著。大家都經常提到,第一個寫這方面的書的人,是一個文化記者,叫做Louis Gonse。1883年他在法國發表了L’Art Japonais這本書,《日本藝術》。這還不能說是一本學術性的書,而是積累各種材料的一本圖片集。奇怪的是,後來這本書流傳到日本,日本的工藝美術家就照著這本書的圖版給法國做各種各樣的工藝美術品,他們以爲他們可以製定這方面的市場。4年以後,在1887年,又是在法國,出現了第一本有關中國美術的書 L’Art Chinois。這本書是Maurice Paléologue寫的,他是一個外交官,也是一個文化人士。這些人當然都沒有任何的訓練,只是根據他們自己的愛好和他們的收藏,碰到所有跟東方美術有關的材料,然後比較隨意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書,還不能算是學術作品。
到了19世紀的90年代,才開始出現一些由學者寫的,有關東亞美術的書。寫這類書的三個代表人物,Friedrich Hirth,Herbert Giles,Stephen W. Bushell,都是當時在中國待著的外國人。Hirth是給海關部門工作的,是一個漢學家。他在德國學過漢語,然後就出來,跟很多當時的中國專家一樣,在清帝國的海關部門工作了好幾十年,同時還在中國的環境裡進行他的學術研究。他最後成爲了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的教授。在這之前,他還在中國的時候,也收藏一些藝術品,尤其是繪畫。他還根據清朝的繪畫寫了一些研究,也包括一些翻譯。
Herbert Giles是一個英國外交官,又是一個漢學家。他也寫過有關中國美術的書,基本上是圖片資料,沒有多少分析;Stephen Bushell的兩本書後來都好像變得很流行。我開始學這行的時候,這些書還被人家使用,但是其實也沒有很深刻的內容。Stephen Bushell是一個醫生,在中國工作了半輩子。
我們回到巴黎看看。歐洲有兩個專門收藏東方藝術的美術館,也都在巴黎,而且到現在還在。一個是Musée Guimet,由Émile Guimet建立,原本建在他出生的城市Lyon,後來搬到巴黎了,一直到現在還在巴黎。這個博物館原本的焦點並不是藝術,而是宗教,現在還能看到這個傳統,後來才發展成爲一個藝術館,但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不少中國、日本,還有東南亞方面的重要藝術品在這個博物館裡。
第二個是Musée Cernuschi。Cernuschi也是一個私人收藏家,到東亞旅行過,買了很多藝術品,後來在巴黎建立了他的博物館。現在是巴黎市經營的。反之,Musée Guimet是法國國家級的東亞藝術博物館,包含了原藏在羅浮宮的東亞收藏。
我們還應該提到另一個人,Hayashi Tadamasa,林忠正。他是一個在巴黎的藝術商人,也是Louis Gonse寫第一本有關日本藝術的書時重要的背景人物,因爲Hayashi給所有這些人都提供材料和知識。如果沒有Hayashi在背後,這個Japonisme潮流,孕育這些書、這些博物館的環境就不太可能形成了。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歐洲年輕知識份子的態度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Virginia Woolf寫得最簡短:「大概在1910年的12月份,人類的個性經過了根本性的改變。」(On or about December 1910, human character changed.)別的作家像奧地利的Stefan Zweig也有類似的體會:「好像年輕的知識份子,明白了他們目前習慣的歐洲的古典的傳統,爲了現代的這麼一種生活已經不足夠,需要開闊視野,不但是在文學和其他的方面,在這個世界藝術,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裡面,也必須做出這方面的改變。」而且他們往亞州,尤其是往中國、日本看,找到了新的啟發。
那麼在這個環境裡面,我們一直能夠看到一定程度上的東方藝術研究的學術化。有意思的是,這好像並不是在法國發生。漢學研究的搖籃應該是法國,但是東方藝術真正進入學術研究的搖籃,可能還是在德國;而第一個出現東方藝術研究傾向的地方,其實是美國,而且這其中有一個日本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Okakura Kakuzô,岡倉覺三,也稱之爲岡倉天心,Okakura Tenshin。他在19世紀末到了波士頓,跟Ernest Fenollosa一起建立了波士頓美術館的東方藝術的收藏,這樣的收藏就變成了歐美各個大博物館的典範。
Ernest Fenollosa在明治時期在東京做過外國專家,在東京大學教過哲學,也就是以美學爲主的哲學。他在那個時候接觸了日本和中國藝術,也寫了一部兩冊有關東方美術的書,是很重要的著作,到最近爲止還有很多人參考。這本著作應該是第一部發行量比較大的、有一點學術態度的、有關東方美術的書,但是Ernest Fenollosa死得比較早。
Okakura Kakuzô在美國的影響對象也不是學術界,基本上是博物館界,而且是在美國喜歡美術的老先生、老太太們,並沒有一下子影響到學術的主流。那個時候,往這一方面的發展還是要在德國才能看到。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一個是Ernst Grosse,也許要翻譯成Große,我不太清楚。Ernst Grosse跟Okakura是同一年生的,原來是一個民族學家,到日本待過,也娶了日本太太,會一些日常日語。還有Grosse的一個徒弟叫做Otto Kümmel。Otto Kümmel是一個藝術史家,原來學的是埃及文,後來轉了行,學了中文和日文。他應該是西方第一個會這兩種語言的藝術史家,真正具備了藝術史和相關語言的訓練,可以做比較高級的學術研究。
Otto Kümmel在東方藝術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是極大的。那一代大學裡面還沒有這方面的教職。他一輩子的工作歷程一直是在博物館界,最後也做了柏林國家博物館的總館長,是柏林所有國家級博物館機構的最高領導。這可惜是在納粹時期發生的,而且Otto Kümmel本身也做了納粹,還可能做了一些壞事情,所以,儘管Otto Kümmel在早期學術發展史上的客觀重要性很大,但是現在的名氣並不是很好。
Grosse和Kümmel這兩個人背後還有幾個恩人,其中一個是Marie Meyer。Grosse是Marie Meyer的養子(adoptive son)。Marie Meyer是一個很有錢的寡婦,收藏東方美術品,在Grosse的影響之下,積累了一批非常有價值的,而且並不是根據民族學標本收藏爲標準的美術品,而是頭一次真正從美學角度出發,用最高的藝術價值標準來收藏的一批日本和中國的藝術品。
在這裡頭起作用的又是剛才已經談到的林忠正,Hayashi Tadamasa,在巴黎的那位藝術商人。Hayashi剛好在1906年死的時候留下了一批作品。Grosse當時用比較合理的價錢從他的家裡給Marie Meyer買了這些作品,Marie Meyer後來又把它們捐給了當時的柏林民族學博物館。
當時的柏林博物館總館長(即柏林所有博物館的總的館長)Wilhelm von Bode,讓Kümmel到柏林去做這批藝術品的負責人,並計劃在柏林建立一個專門的東方藝術的博物館。但是因爲後來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事情就耽誤了,沒有一下子做到,可是最後還是做到了。
我還要提到另外三位在那一代起了比較重要作用的人。一個是Oskar Münsterberg。他原來是一個工程師,可是他喜歡上了東方美術,於是到日本和中國廣泛旅行,寫了一套很厚的《東方美術史》,第一本是有關日本的,第二本是關於中國的。這是第一次有人試圖根據「風格」的變化而寫出的東方美術發展史,不關心藝術家個人。儘管他具體上有很多錯誤,而且他也不會說這方面的語言,但在當時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突破。
另外兩個是Woldemar Freiherr von Seidlitz,還有Julius Kurth,主要研究日本藝術,他們都有這方面的作品。Seidlitz還有一個重要的著作,他早在1905年就發表了一本小書,書名是《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東方藝術的博物館》。他當時就明白中國和日本這些美術史的傳統,不能當做民族學的一部分來研究。中國的繪畫、日本的繪畫、雕塑等等,不是民族學的標本,而是跟歐洲這些最高等的藝術品同等的,必須發展一套理論、一套學術方法,來真正地從它裡頭研究出它的美學和價值觀,還要研究出它的視覺習慣(visual conventions)。這當然是藝術史的功勞,建立起這樣的基礎,就可以把藝術品當作寫歷史的一個材料。這樣的傳統,我們稱之爲藝術的一個傳統,雖然在東方國家有很長久的研究,也有很多的著作,但是這麼一種科學的研究角度,在那個時候的東方國家還沒有發展出來。所以Kümmel、Grosse、Münsterberg,還有Seidlitz和Kurth,他們對西方以外的,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這些藝術傳統的期望,還有他們如何理解、怎樣研究東亞藝術的角度,都是很新穎的。這些貢獻要等到下一代才真正開始發揮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就開始有一批人在大學裡面專門研究東方藝術,全都是在德語界,而且這方面的發展方向很有意思,就是「從上往下」。第一個拿到東方藝術史研究學位的人,沒有拿到博士學位,而是拿到Habilitation(德語國家教授資格考試)。在德國系統裡,Habilitation是比博士還要高的一個學位。當時當然還沒有教這方面的教授,沒有關係,在德國的大學系統裡面,只要能夠找到一個願意做導師的教授,那怕不是這個教授的專業,學生可以隨便發展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所以在1912年,Otto Fischer就向Göttingen大學提交了他的Habilitation論文。Otto Fischer的論文是有關中國山水畫的,是西方第一次有關於這個題目的學術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發表成書。這本書現在在很多圖書館還能看到。
第一個博士學位論文,用比較廣的意義來看,也許是Arthur Wachsberger於1914年在維也納大學提交的論文,這個論文的題目是新疆的石窟寺藝術。當時剛好有這方面的材料,一部分被歐洲的調查團掠去英國、德國還有法國。Wachsberger就寫了這方面的博士論文。這是第一篇以從中國領土出土的材料爲題撰寫的博士論文,儘管當時的佛教藝術可能被普遍認爲是印度藝術傳統的一部分。
1917年,Leipzig大學的漢學教授August Conrady指導了一位博士(Otto Burchard)畢業。他寫了中國繪畫方面的漢學博士論文,寫了一些有關繪畫的文獻內容。Otto Burchard後來在柏林經營了一個當時最現代的藝術畫廊,他變成了Dadaist的志願者,在這張照片中就能夠看到他的周圍都是Dada這些藝術家,但後來Burchard還是以東方藝術爲主。他在納粹時期以前就移民到中國,在中國北京經營一個專門賣中國傳統藝術的畫廊。Otto Burchard是一個眼睛特別好的專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一些美國這方面的專家到了中國,就找Burchard當他們的導師。
第4個在學生名單上的是Karl With,現在幾乎被忘記了,可是也很重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到日本做了調查,而且還在奈良照了各種佛像的照片,根據這批材料,在維也納準備了一個博士論文。剛好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做了4年的戰士,後來活下來,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好結束的時候,回到維也納提交他的博士論文。這個人的學術歷程一直在博物館界,但是他最後也只好離開德國,30年代到了美國,而且在我現在所在的UCLA當教授。他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認爲自己是東亞藝術的專家,而是世界藝術的專家。他對藝術的瞭解也很獨特,我就此專門寫過文章,現在沒有時間細談,但是他的博士論文還是有關日本藝術,後來也寫過書。
Alfred Salmony原來是With 和Wachsberger在維也納的同學,但是他後來到Bonn大學寫出他的博士論文,也是寫日本的佛教雕塑。
Ludwig Bachhofer是第一個既寫了博士論文,又同時寫了Habilitation的人,兩篇論文的題目都是東方美術,而且都在慕尼黑,都是在Heinrich Wölfflin的指導之下寫的。Heinrich Wölfflin是當時,而且可能一直到現在都被認爲是20世紀最重要的美術史家。Ludwig Bachhofer的研究方法也深受Wölfflin的影響。

另外在這張投影片裡談到的這幾個人,除了Werner Rüdenberg沒有照片。Rüdenberg也沒有當過教授,提到他只不過是因爲他編了第一個比較大的中德字典,是Alfred Salmony的舅舅,後來移民到倫敦。Salmony和Wachsberger應該都是猶太人,都離開了德國。Bachhofer的夫人是猶太人,因此他也離開了德國。Bachhofer最後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Salmony是紐約大學的教授。With我剛才已經說了是UCLA的。Burchard也是猶太人,在北京,後來在美國和英國都辦了畫廊。Wachsberger也是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到當時的巴勒斯坦。這其中唯一沒有被迫離開德國的是Otto Fischer,但是Otto Fischer也走了,他去了瑞士,做了巴塞博物館的館長。
所有這些早期的學生們沒有一個後來留在德國。留在德國的是Otto Kümmel。他們的導師是當時最傑出的藝術史家,也是最奇怪的藝術史家:Strzygowski。Strzygowski原來是維也納大學一個系裡面的兩個教授之一,後來他跟另外那一位合不來,就分出來建立自己的學系了。他主張超級的日耳曼人至上主義,還不能說nationalist,應該是chauvinist。他認爲人類純粹的藝術精神都被希臘羅馬傳統弄壞了,唯一真正有價值的是日耳曼古代民族的精神,而且爲了把它恢復過來,最好的方法是盡量研究希臘羅馬以外的各個地方的藝術,也包括中國、日本。所以他是可以接受中國和日本美術的專家,像Alfred Salmony、Karl With那樣,在他的指導之下,做他們的博士論文。Strzygowski後來也跟希特勒走得太近,現在名氣極壞,可是對東亞藝術研究的發起起了很可觀的作用。
Bonn大學當時也有幾個人,儘管完全不是東方藝術的專家,但是他們感興趣,而且願意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其中一個是Wilhelm Worringer,他原來研究過中世紀美術,後來對當時的當代藝術感興趣,據說他發明出Expressionismus(表現主義)這個詞。在20、30年代,主要是20年代,他的門下有好幾個人出來研究歐洲以外的藝術。
Paul Clemen主要的專長是德國Bonn這一帶的中世紀建築,非常傑出。可是他也對東亞藝術感興趣,比如說他看到了日本佛教的雕塑和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藝術之間的一些共同點,他希望他的學生們認同和研究這個,而且是用嚴謹的美術史的方法去研究這方面。他跟Worringer一起培訓了這些學生。
Wölfflin,大概是20世紀在美術史的方法上貢獻最深的學者。他有好幾個後來研究東亞美術的弟子,唯一一個在他的指導之下,既得到博士學位,又得到Habilitation的是剛才已經說的Bachhofer,後來在芝加哥了。
剛才我說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柏林就有人特別希望建立一個東方藝術博物館,而且已經有收藏,這個收藏是以美學的標準收集起來的,可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沒有及時做到。其實德語界第一個東方美術的博物館是1913年在科隆(Köln)建立起來的博物館(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是Adolf Fischer和他的夫人Frieda Fischer的私人收藏。他們自己去日本和中國,買了各方面的藝術品。當然他們得到的顧問不像Marie Meyer從Grosse和Kümmel得到的訊息那麼可靠,但還是積累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收藏。
這個博物館的建築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完全被炸了,可是收藏品仍保存下來。我小的時候,照片中這個可能是中世紀城門的塔樓裡還有它們的臨時展地。1970年才有一個日本藝術建築師Maekawa Kunio建了新館。新館後來還增加了收藏,但是Fischer夫婦的東西還在。
柏林那邊要等到1926年,他們期待已久的東方藝術博物館才終於開幕。它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博物館,而是Museum of Applied Arts(工藝美術博物館)裡的一個部門。
當時柏林有好幾個人參加東亞美術的研究活動,不單是Kümmel。Kümmel當然最重要,Kümmel是在博物館裡面做主的。可是還有其他人。比如說Curt Glaser,他原來是一個醫生,可是後來在Wölfflin那裡也拿到了美術史博士,在20年代做了柏林藝術圖書館的館長。柏林藝術圖書館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非常棒的,專門收藏藝術方面書籍的圖書館。Glaser也被逼迫離開德國,他原來還有非常重要的藝術收藏,都被納粹沒收了,到2012年才還給了他的後代。Glaser寫了有關中國、日本藝術的書。另外作品更多的是William Cohn,他原來是一個哲學家,後來也專門研究中國和日本,還有印度、東南亞的藝術。William Cohn的著作很多,還長期編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它是全世界第一個專門有關東亞美術的學術刊物。從1912年開始編,後來改了幾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停刊了,2001年才復刊。在20年代中期以後,又有第二個學術刊物叫做Artibus Asiae,一直到現在還很有名望。它的總部從1925年到1939年一直在柏林,後來在1944年搬到瑞士,又在1992年搬到了紐約。但原來的總部是在柏林,出版在萊比錫。
柏林在1926年又建立了一個東亞美術研究會”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聚集了所有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學術界人士,還有學術界以外的收藏家之類的。這對他們建立這些博物館收藏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可以說是打好了群眾基礎。這個學術會議一直到現在仍然存在。
1926年,Kümmel專門把東方藝術品放入藝術展覽的展覽室。展覽終於在工藝美術博物館開幕了。當時被認爲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展覽,收藏很豐富,而且質量比較高。
照片中的這個建築物其實是我的太祖父建的,Martin Gropius(1824-1880),現在叫做Martin-Gropius-Bau,是柏林國家級博物館機構的一個做臨時展覽的場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毀壞了,幸虧收藏都拿到煤礦裡面去保存,沒有放在那裡面。但是這些收藏後來被俄國人沒收了,一直到現在都在聖彼德堡冬宮博物館的地下室裡面,已經有快80年沒有公眾看到,但是東西還在,有一些專家看到了。現在的柏林東方藝術博物館,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建立的,完全是新的收藏。
Kümmel有三個原則在當時是很有突破性的,跟傳統的像宗教,或者比較接近於民族學的博物館展覽方式完全不一樣。
Kümmel認爲收藏品必須能給中國、日本和韓國(他還包括韓國,儘管當時韓國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他看出韓國作爲一個獨立的文化傳統的重要性)這三個國家作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基本介紹,而且要平衡。意思是收藏中要包括各種媒體的藝術品,也要有各種時代的、不同風格的、不同材料的東西。他跟很多歐洲展出東方藝術的機構(一直到現在也是)不一樣的原則是:最重要的是繪畫。他還沒有說最重要的是書法。如果真正體會中國傳統美術觀的最高處,可能他會說到這一點;但是他也知道,西方的觀眾很難能夠真正欣賞東方的書法。反正他就把繪畫放在最高的位置,而且最重要的範疇不是別的,而是藝術價值、美學價值。民族學家不會這樣,民族學家會考慮收藏是不是有代表性,比如說從題材來做選擇,或者說要中國每個省都有一些具代表性的作品。Kümmel完全不關心這個,他就要好東西。
作爲博物館的專家就是這樣的態度。所以在這一方面,Kümmel跟專門展出歐洲藝術的博物館的館長是同樣的態度,而跟展出歐洲以外的東西的民族學博物館完全分開。Kümmel原來當然不是一個教授,好像也沒有拿到Habilitation。原則上沒有Habilitation,就不能在大學裡面做博士生的導師,但是他最後也在當時的柏林大學裡面教了課,也培養了不少學生。
奇怪的是在30年代以後,好像他在納粹時期之前,是未被認爲有資格培養博士生的。就是因爲他在1933年以後參加納粹黨,而且在納粹的制度裡面得到很高的位置,所以就得到這種資格。他好幾個學生後來都在各個博物館做過工作,也可以說是一條「死路」(cul-de-sac),其中沒有一個後來還培養過學生的,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也就只能這樣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就沒有一個大學有專門教東方美術史的教員。所以這些學生有的在德國,有的在國外,都在博物館界裡面有了他們的歷程。而且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女性,在這之前都是男性。
我另外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討論了20、30年代德國大學畢業的4位東亞藝術史家,後來長期在中國待著。其中第一個是Gustav Ecke,他早在20年代就已經到了中國,他原來的背景不是學東方藝術的,但是到了中國就很快進入了這行。他是Bonn大學培養出來的,是Clemen的學生,懂建築分析,後來對中國建築還有家具的研究做了很重要的貢獻。1949年年初,他和他的太太趕快離開了中國,後來在夏威夷大學做了教授。
這四個德國學者當中最後到中國的一個也在後來到了美國,Max Loehr(羅樾),哈佛大學的中國美術史的泰斗。是Bachhofer(就是Wölfflin的學生Bachhofer)在德國唯一的學生,而且是納粹份子,被納粹政府派遣到當時被日本佔領的北平,做一個所謂的德國文化研究所的所長。這個研究所應該也做別的活動,我不細談,反正現在也很難知道到底做了什麼。總之有強烈的政治任務,同時也發展了他在中國藝術方面的學術。他在Bachhofer的指導之下學到了這方面的知識,但是他這方面比較大的貢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做出的。他戰後逗留在北京,好像在清華教德語,可能還教了一些美術史,反正最後短暫回到德國之後,就流亡到了美國,在密之根和哈佛陸續當過教授。羅樾的學術,客觀的來說,好像一直到最後都沒有完全脫離納粹的藝術觀,但這個問題還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今天不能細談。
民國時期待在中國的另外兩位女學者,最後乖乖回到德國了。Eleanor von Erdberg在一個培養工程師的科技大學還做了教授,她的大部分學生都是建築師,同時她一直到最後還繼續發表有關中國藝術的著作,主要面對普通讀者。儘管在中國待了14年,但好像不怎麼會說漢語,學術水平可能也比較一般,但是也不能說沒有做過貢獻。她是這4個人之中唯一寫了回憶錄的,這本回憶錄寫得非常有趣(儘管,和所有的回憶錄一樣,內容並不全部可信)。
另外一個Victoria Contag可能是這4個人當中最接近於中國傳統藝術界的圈子的。她是一個外交官的夫人,其實我應該說,她原來是在Kümmel那邊做過助手的,學過東方美術。到中國旅行,在中國待了一段時間,認識了一個在上海的德國外交官,跟他結婚了,後來就長期在中國進行學術研究,還跟中國學者王季遷一起編了一本有關藝術家圖章的著作。這本書一直到現在大家都還在使用。
Victoria Contag認識當時上海、蘇州那一帶所有重要的藝術家,而且看到的藝術品和繪畫比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多得多。她是文人繪畫的大專家,後來也寫了書。回到德國以後,還在美因茲大學(University of Mainz)任教過,可是沒有當教授,後來也就死了。她在中國積累的一大批收藏,後來都被賣掉了,現在分散了,比較可惜。當時德國的機構其實有機會買,可是沒有買,現在很多都在美國。好。不再談他們,反正這方面我已經寫過文章。
這是Ecke和他的太太,比他自己年輕得多、一個很漂亮的北京太太,叫曾幼荷,是一個畫家。曾幼荷於2017年在北京高齡去世,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藝術家。Ecke在她還非常年輕的時候看中了她,看出了她高級的才能,就跟她結婚了,讓她接觸西方當代藝術,非常獨特。
到了1945年,Kümmel當然就完全不行了。他還在,可是博物館就炸了,收藏被拿到俄國去。他自己做過比較高級的納粹份子,當然就不能再恢復工作。他的學生們有的也是做過納粹,有的離開了,反正也不能真正地延續原有的傳統,基本上是從零開始,就是東亞美術史在德國的研究基本上是1945年以後,從零開始的。
能夠重新開始的原因,是當時有一個叫做Dietrich Seckel的人突然出現了。這個人在1935年納粹時代初期就離開了德國,去了日本,當過德語老師。他在日本待著,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日本就學會了日本美術。他原來的背景是學文學的,但是學會了日本美術,回到德國的時候就提交了一個Habilitation的大的論文,有關日本的佛寺。海德堡大學就只好接受了,反正有了這個Habilitation,而且是合格的,不能不讓他保留這個學位,然後他就在大學裡邊了。當然沒有教職,但是他就在,反正凡是有Habilitation的人,爲了能夠有一個教職,必須一直在大學裡邊,每年都教書,一直到能夠拿到一個教授的位置。
Dietrich Seckel好幾年都在圖書館打工,一面打工,一面在海德堡大學上這方面的課程,最後海德堡大學就只好給他設置了一個東方美術史的教職。這個教職在德國是第一次設置,一直到現在還存在。他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是:Helmut Brinker後來到瑞士,在蘇黎世建立了東方藝術史的研究;Lothar Ledderose在海德堡繼承他的老師Dietrich Seckel的位置。Roger Goepper也很重要,他原來是學漢學的,研究中國書法的;但是後來他找的工作就是做Köln東方美術博物館的館長,一直做到最後。他一面做館長,一面在Köln大學教書。他也教了一批學生,也有了教授這麼一個稱號。這4個人可以說是在50年代以後,完全恢復了,而且重建了德國研究東亞美術的傳統。
現在這個狀況當然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現在又有很多中國的學生在那兒學習,甚至有中國的助教授在那工作。還有一些學生回到中國。現在中國也有西方式的美術史學科,儘管這個歷史還不是很久,但是這幾十年來也開始有了。
然後當然Köln的博物館還繼續存在,柏林呢,東柏林從1952年開始,把他們能夠找到的東方藝術品也收藏起來了,在Bode Museum,就是他們的工藝美術博物館的一個小地方,有了一個東方部門;西柏林稍微晚一點,1970年在一個新建立的博物館群裡,也有了一個東方的部門。那個收藏是當時新買來的,幸虧當時在國際的藝術市場上還能夠買到比較重要的作品,所以這個收藏到現在也已經是比較值得注意的。這個博物館現在已經關閉了,它首先跟它的印度博物館合併,變成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後來關閉了,要搬到新建立的所謂的Humboldt Forum。Humboldt Forum像原來德國第二帝國皇家的皇宮,其實那個皇宮已經被東德政府拆掉了,這是一個複製品,從後面一看是現代建築。它在兩德合併之後就重建了,原來2019年就要開幕,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幕。據說現在已經建成了,隨時可以開幕的,但是現在因爲疫病的原因還一直推遲。可能從今年年底以後,大家能看到,但是能看到的就是原來民族學博物館的東西,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買的東西,Kümmel的那個收藏仍然在聖彼德堡。
那麼我再總結一下,東方美術史研究如何變成了一個學科呢?先從愛好者開始,第二,建成一個博物館,然後變成博物館的一個主題,然後進入了學術界,在學術界有趣的是,從上面開始,先是有教授資格的,然後再有博士學位的。博士生沒有工作機會,只好進入博物館工作,到了兩代以上,才有了第一個真正的教職。現在在德國有兩個教職,一個在柏林大學,一個在海德堡(海德堡現在已經有兩個東亞美術的教授,一個教中國,另一個教日本)。科隆(Köln)可能有這方面的課程,但是沒有一個專門的教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東方美術在西方的中心已經不在德國,而是在美國,是因爲很多原來在德國的學者去了美國,在美國又培養了新的一代,包括很多從中國出生的學者。將來東方美術史的中心,當然應該是在中國和日本,但是據我的理解,這個時間可能還沒有完全到。謝謝大家。
張健教授:
好,謝謝羅教授。羅教授在一個極爲廣闊的背景之下,介紹了歐洲研究東亞藝術史的傳統,講述了現代的東亞藝術史學科的成立和演變的過程,綱目咸備,圖文並茂,羅教授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我們深受啟發。現在我們就請張隆溪教授來發表評論。
張隆溪教授:
我就是簡單地講幾句。首先很高興,跟羅泰也是很久沒見面了,所以今天很高興能夠在網上見面。張健教授也提到,我們在80年代之後都在哈佛做同學,雖然我們不是一個系的,但是經常來往,而且做了教授以後也經常來往,所以我對羅泰很瞭解。羅泰是非常非常嚴謹的學者,在這一點上可能有德國學術的傳統,他做什麼事情都非常嚴謹,材料非常詳實,說任何一個東西都是有依據的,而且把什麼東西都搞得非常清楚。他今天講東亞藝術史在歐洲,主要是在德國或者德語系的國家,包括像瑞士,還有像奧地利等等,學術的脈絡一代一代的講得非常清楚。他最後的總結,(這個脈絡)一開始是一種喜好,是業餘的,就是做外交家或者是商人或者是工程師,因爲喜歡東方的藝術,然後收藏,然後逐漸地再變成一個學術的領域。他其實一開始就講,可以把研究東亞藝術看成東方的研究,或者說整個漢學研究當中一個特別的領域,從這個學術發展的途徑就看得出來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講座,不光是講當時歷史怎麼樣,這當中對我們以後有很多啟示。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幾點,一個就是從歌德開始講,在德國,歌德當然是一個文化的巨人,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現在做文學的研究,比如說講到歌德對於世界文學就非常非常重要。當時在19世紀初,歌德已經年齡很大了,在歐洲有非常大的影響。對於當時的歐洲學者來講,他的眼界非常開闊,對於東亞、對於非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興趣。所以他提出來的「Weltliteratur」(世界文學),就是在跟Eckermann談及最近在讀一本中國小說的譯本時提到的。這個概念對於現在研究世界文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確實可能就像你講的,他可能沒有見到比較高級的中國藝術品,所以他們對中國的藝術評價還是比較低。
比歌德更早一點,像Giambattista Vico(維柯),他在《新科學》裡面可以說是開創了近代社會科學的各種方法。他對於繪畫也是這樣的看法,覺得中國的畫沒有透視,完全不像西方的繪畫那麼寫實,是非常粗糙的。所以他們在當時對於中國的瞭解還是有限的。可是你講到後來像Fenollosa在日本和美國於這方面就有很大的貢獻。尤其講到Otto Kümmel,他雖然是納粹份子,但是他在研究藝術方面,不僅自己有成就,而且培養了很多很好的學生。
當中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培養的學生很多都被迫離開德國,因爲凡是猶太人或者太太是猶太人,跟猶太人結婚的,就必須要離開德國,這對德國的學術發展確實是很大的傷害。我記得我跟Martin Kern講過,我想請他來講一下德國的漢學,他還沒有同意來講,但是他寄給我他的一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說,在德國很少人講納粹德國的時候對於漢學的破壞,他說他是第一個,就以很長的一篇文章講很多猶太人研究中國的漢學家都被迫離開德國。其實這個不光是漢學,或者應該說是整個學術圈。最重要的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也是離開了德國。那麼在文學研究當中,我們講的Erich Auerbach,Leo Spitzer 都是非常重要的學者,在當時都被解除了教職。Auerbach在Marburg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教授,不得不離開德國去了伊斯坦堡。他最重要的一本書Mimesis就是在伊斯坦堡寫的。這些人後來都到了美國,所以在戰後,美國成爲學術的中心,其實跟德國排猶有很大的關係。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叫做 Hitler’s Gift,就是說美國的學術發展其實是希特勒送的一個很好的禮物,因爲他把很多猶太學者都從德國趕走。
你講的其實跟當時整個世界的歷史非常有關係,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發展起來,首先在歐洲引起重視,所以Japonisme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然後日本自己也起到了作用,比如你講的林忠正,對於研究東方的藝術跟在德國發生的一些影響。還有Wölfflin,當然是20世紀藝術史當中有非常非常重要影響的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後來你講了很多,具體的我就不太熟悉了,我只知道一些大概,所以我也學到很多東西,非常感謝。
我想最後我不能講得太長了,我覺得如何把東亞藝術史的研究作爲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有很多可以發揮的餘地。我想今天羅泰給了我們一個啟示,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會有問題向羅泰來請教的,我就講到這裡。
張健教授:
羅教授您是不是要先回應一下?
羅泰教授:
沒有什麼具體要回應的,非常感謝,講得非常好。還可以拉回到Vico那邊去,這個很有意思。確實中國繪畫裡面缺乏透視的這麼一個偏見,是一直被人提到的。雷德侯(Ledderose)先生好像跟西方藝術史的專家還一起開過課,詳細做過這方面的對比,然後高居翰,James Cahill,好像還發現了一個17世紀的中國藝術家,他還真有透視的感覺,叫做張宏。不是很有名的,但是他確實掌握了透視。是否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就不好說,但其實如果我們細看古代的藝術,也不是完全沒有。漢代的朱鮪祠,在山東的朱家祠,就完全有透視的表現。唐代敦煌石窟裡面也有,在那些西方淨土、這些大的圖畫裡面,當然是有透視。所以中國藝術家不是不會做透視,他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不願意做,就是要強調別的了。
張隆溪教授:
說得很對,其實我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很短的一篇文章。在沈括的《夢溪筆談》裡面,專門有一段說李成,李成是唐代的畫家。沈括說:「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就是說屋簷好像是從下往上看上去,「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就是說李成畫的畫完全用透視法,他屋簷畫得很高,你站在地上看見屋簷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沈括有個評論,他說:「此論非也」,他認爲李成說得不對。他說:「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畫山水是從一個大的上面來看小的,「如人觀假山耳」,就像一個人看假山一樣,什麼前後都可以看到的。他說「若同真山之法」,如果真的像看真的山一樣,「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如果你是真的站在地上看著山的話,只能看到一重山,不可能看到幾重山的,「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也更看不到溪水裡邊、山谷裡邊的事情;「又如屋舍」,就像房屋一樣,「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如果是畫的話,你只能看到一個地方,中庭是怎麼樣、後院是怎麼樣,你看不到的。
他說:「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這完全是透視,但你如果人站在東邊,你看到遠處西邊的山應該是遠景;「人在西立,則山東卻合是遠境」,如果人站在西邊,東邊的山應該是遠景。「似此如何成畫?」如果這樣的話還叫什麼畫?他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不是不懂透視,但是中國的美學觀念就是畫畫不應該這樣畫。他說「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應該是這樣。沈括是宋代的,可以看到宋代的人其實已經懂透視,但是覺得畫畫不應該用透視法。
羅泰教授:
就是就是,說得完全正確。
張健教授:
下面是答問的環節。我已經看到有不少聽眾提問,那麼現在請助理陳康濤先生來讀問題,主持這個環節。
陳康濤助理:
好的,下面我們就進入到聽眾的提問。第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請問老師,爲什麼歐洲在研究東亞藝術的時候,會將中國與日本聯繫在一起,甚至在一些圖像中,兩個民族的元素經常被混在一塊使用?
羅泰教授:
對。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可能跟18世紀以來的這些文化溝通傾向有關係。中國的藝術品傳到歐洲,主要是陶瓷,還有漆器之類的,歐洲早期可能根本分不清什麼東西是中國的,什麼是日本的。
到了19世紀,日本政府好像花了比較大的力氣,也就推動了他們的工藝到歐洲去,這是Japonisme的動力之一。在明治維新之前好像已經有這方面的傾向,之後他們利用這些工藝做文化宣傳。中國政府沒有這樣做,在當時就根本沒有條件這樣做。
於是日本也就變成西方人能夠比較容易接觸東方藝術的地方,然後到了日本當地,能夠看的當然不只是日本的東西,在日本也能看到很多中國的東西,這些中國的東西一直在日本,而且日本的藝術也受到中國一定的影響。所以像Okakura或者Hayashi或者Grosse、Kümmel這些去過日本,既研究中國,又在日本研究日本藝術的人,他們想當然地帶有一些日本文化對中國藝術很強烈的態度和偏見,長期影響到了歐洲對東方藝術的瞭解。真正開始從裡面理解中國藝術是後來的事情,但是這都不是必然的,跟當時歷史的客觀條件有關係。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個問題是:請問老師,現在美國的東亞藝術史的研究,仍然是以繼承德國的影響爲主嗎?還是已經多元化起來了?
羅泰教授:
這一點我並不完全瞭解,可是我的印象是,藝術史這整個學科的基本傳統是在19世紀的德國形成的,而且是在歷史和哲學這兩個系的中間形成出來的。張隆溪教授剛才也說了,後來流傳到了美國,變成美國美術史研究傳統的主流。在30年代,這些從德國出來的大學者到了美國,不只是研究東方的,還有研究很多方面的非常偉大的學者,包括一些藝術史家,像Panofsky後來到了普林斯頓。他們出來之後,就完全改變了原來美國美術史研究的傳統。我估計德國的這一套,通過他們在美國建立的這一套傳統,一直到現在的作用還是很大;好像沒有幾個美國的大學美術史系不要求他們的研究生會德語,至少搞西方美術的研究生,都必須學德語。
張隆溪教授:
羅泰,你還記得Chris Wood?
羅泰教授:
記得。他最近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
張隆溪教授:
Chris Wood就是美術史畢業,也是哈佛的同學,他後來在耶魯做了藝術史的教授和系主任,最近他到了紐約大學,很奇怪,他到紐約大學做德語系系主任,他是美國人,但是他當然受德國影響非常大,因爲他就翻譯了很多Wölfflin的東西。
羅泰教授:
對,而且他最近寫了一本書A History of Art History,真的是一個傑作。不錯,非常不錯。所以這個傳統還在,我之所以稍微有一點猶豫,是因爲最近20、30年,藝術史和所有的人文科學一樣,受到相當嚴重的後現代主義的影響,這個到一定程度可能就削弱了原來從德國流傳出來的傳統。現在比如說gender studies或者 post-colonial那些方法論裡面,可能就不太能看出藝術史裡面原來德國的源頭。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請問羅泰老師,在講座開始的時候,您也提到了中國音樂的研究還仍然在學科建設的過程中,並且我們知道您本人是做中國音樂起家的,請問您認爲這次講座的回顧可以爲我們日後研究中國音樂提供什麼樣的借鑒意義呢?您認爲中國音樂研究要作爲一門學科,就現有情況而言,還需要從哪些方面做哪些工作?謝謝。
羅泰教授:
謝謝,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是我沒有學中國音樂,我只是研究中國的樂器,這是有區別的。我研究的樂器所演奏的音樂已經不在了。相比中國音樂,我稍微再更懂一點西方音樂,因爲我從小有這個愛好,但這僅僅是愛好,並不是學術;但是如果我剛才有關藝術史的理解真的能夠當做一個典範的話,那就可以期待將來中國音樂學在西方的發展可能也有類似的途徑。它要先打好群眾基礎,要建立公眾對中國音樂的欣賞和瞭解。有了之後,就很容易想像,會有這方面專門的建設,當然不是博物館,應該是音樂廳之類的,還有樂隊,最後也許就能夠進入學術史比較接近主流的地方。當然現在已經有一些民族音樂系,就是Ethnomusicology,包括我們 UCLA在這方面都有很好的專家,可是畢竟特別少,比搞中國美術的專家少太多了,少得可憐。所以這裡可以期待,我們將來還能有所發展,但是對不起,我在這方面沒有很具體的推薦。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提到,有一篇論文裡面提到了19世紀女性趣味對於Japonisme,日本風潮的影響,那麼在東亞藝術收藏的研究中,是否存在gender difference呢?例如說收藏青銅器是個男性的趣味,而收藏繡畫是更女性的趣味。
羅泰教授:
比如說我剛才介紹的兩個女學者,一個是 Victoria Contag,當然是一個研究繪畫的大專家,但是Eleanor von Erdberg研究的是建築和青銅器,而且寫了這方面的著作,我在這方面看不到一個很絕對的對比。現在在德國研究中國青銅器,尤其是在研究中國金文方面做的最好的,是一個女學者。而且不只是一個女學者,在德國不止一個,都是有本領的。說不清楚,所以這一點我真的說不清楚。
我剛剛沒有提到,我最後的屏幕上是4個男生,但如果我們延續到當代,比如說德國兩個博物館的館長,一個現在是空著的,但是Köln的那個早就已經是一個女館長;兩個大學的教授,柏林大學和海德堡大學東方美術史的教授,三位都是女教授,所以在性別方面已經有一定的轉變。學生們也是,現在大多數都是女學生,以前未必如此。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個問題是:請問羅泰老師和張隆溪老師,你們分別如何理解中國書法在藝術史裡面的地位?中國書法是否比中國音樂更難與其他文化溝通對話?
羅泰教授:
隆溪你要不要回答?他也問你,你可能更懂這個,你正好也會寫書法。
張隆溪教授:
我覺得他已經講到了,可能書法對於歐洲的一般觀眾來講是更難去欣賞或者理解的,因爲書法當然跟文字有關係,而且不光是文字。在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阿拉伯大概也有這樣的書法,對吧?當然西方也有calligraphy這個說法,書法這個詞本來就有,但是在現代社會,因爲都是用電腦,大概用寫的都很少,但是書法在中國一直是個藝術形式。從文人的角度來講,書法當然是非常高雅、非常重要的。像王羲之,被稱爲「書聖」,在中國的文化地位是非常高的,絕不亞於最好的畫家。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書法在中國佔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確實,我想要跨過語言和文化,在別的文化當中去接受是很困難的。比如我自己雖然喜歡書法,我也知道阿拉伯也講究書法,可是我看阿拉伯的寺廟,比如說我去印度,Taj Mahal上面那個很漂亮的字,我覺得還是沒辦法真正地懂。因爲你不懂得語言,你只覺得這字比較好看。很多清真寺上面都有這種阿拉伯的書法,但是我就沒辦法去評價它,沒辦法去看哪個好哪個不好。在我看來都很漂亮,但就如此而已,所以很難有一種真正的理解。我相信中國的書法也是這樣,不懂中文,對於中國文化瞭解不是那麼多,就很難真正瞭解中國的書法。所以羅泰一開始講,一種藝術要發展,首先要有個群眾基礎。我想書法的群眾基礎是最難的,一般不懂中文又不懂中國文化的人,看書法不會知道是什麼,所以確實很困難。
羅泰教授:
紐約在50年代以後,有一些藝術家把東方的書法當作一種抽象藝術來欣賞,這當然完全是誤解。這是一個很可笑的誤解,不應該是這樣的,然後他們還根據中國的書法自己亂寫,亂做抽象的藝術。
張隆溪教授:
徐冰不是就專門做這個嗎?
羅泰教授:
徐冰又不一樣,他又更高級,而且他最後的觀眾還是中國人,他始終是從書法藝術開始的。那些人不懂書法,不想學漢語,也不想練字,反正他們覺得書法從視覺方面比較接近於抽象的藝術,這當然是荒唐的。但是,也許在這種狀況之下,也會引起某一批觀眾突然間明白,不能這樣做,還是要學,然後從這個基礎上發展connoisseurship(鑒賞力),由此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理解。反正在美國和歐洲的東方美術史界,現在有一批學者不但研究中國繪畫,而且有一些就研究書法的,包括剛才說的雷德侯教授,他70年代的博士論文已經是有關書法的,而且上述Goepper教授是研究《書譜》的。當然《書譜》是一個理論作品,他是從漢學方面研究的。反正有一些人進入了這方面的研究,但是一般的觀眾看書法展覽,理解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小,這一點說得對。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謝謝羅泰教授介紹了德國的情況,實在學到了很多。想請教您,英國對於東方藝術史的研究情況如何?英國與德國之間可以比較嗎?
羅泰教授:
這個有意思的是,好像英國大學界發展藝術史的時代比較晚,劍橋和牛津好像有這方面的講座,都是從20世紀的後期才開始。當然倫敦有Courtauld Institute,還有Warburg Institute,但其實Warburg也是從德國傳過去的,完全是傳過去的。儘管英國博物館都比歐洲大陸的很多地方強很多,而且東西好得不得了,但是真正脫離了簡單的Connoisseurship,脫離了目錄學或者民族學對文物理解的水平,真正透入藝術史嚴謹方法的這麼一個學科在英國得到發展,其實也要到希特勒時期,靠當時從德國流出來一些人才。這方面英國跟歐洲大陸還不完全一樣。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想請問羅泰老師跟張隆溪老師,中國學者和海外學者研究東方藝術的方法和內容有什麼差異?他們各有哪些側重點?你們如何看待現在中國跟國外對於中國藝術史研究的對接與交流?謝謝。
羅泰教授:
我希望張隆溪教授也會發言,我先說一個簡單的事情,跟這一系列演講總的題目有關係,就是說我們在西方做這方面的研究都是通過翻譯,必須把所有的詞語都拿到另外一個語言的語境裡面去,這樣便逼迫我們對背後的事實作另外一層的思考,跟中國人研究西方藝術的過程一樣。
如果是作爲中國人研究中國藝術的話,當然就更加接近,就不用經過這個環節。這有好處,毫無疑問就可以直接理解,有一些直接認同,我們從外面進來的是永遠得不到的;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有一些unexamined assumptions,沒有經過批評精神考驗的一些思維方式一直會在裡面,所以最後的學術結果會有不同的地方,這是不能避免的。隆溪怎麼想?
張隆溪教授:
我對於國內中國學者研究中國藝術其實並沒有什麼瞭解,我不是做這方面的,但是我很同意剛才羅泰講的話。在我看來,在我們當代這個時候,不是說古代了,在21世紀,我們現在作爲中國人自己研究中國自己的東西,都要有一個很開闊的眼光,起碼把它放在東亞這個角度,比如從隋唐以來一直到19世紀,中國的文字在東亞是通用的,中國有很多東西也在日本、在韓國、在朝鮮流通,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要研究中國自己的東西,需要一個更大的眼光,更大的範圍。從學術方面來講,我覺得需要這種思考。
剛才羅泰講得很對,就是說一個外國的漢學家來研究中國東西,每一個名詞都要思考一下什麼意思。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思考,有的時候當然很容易,比如你要討論古代的文學就直接引過來,就不需要翻譯,但是對文字本身的理解,有的時候反而很容易就一下子跳過去了,沒有鑽得很深入。這方面我想張健教授最有體會,因爲他對於《文心雕龍》很有瞭解和研究,所以他對這個詞語是怎麼回事情,我想很多可以講,張健要不要你要講?
張健教授:
還是你們來講,然後給聽眾來提問,給大家更多的機會。
陳康濤助理:
那我們繼續聽眾的提問。羅教授您好,今天您談到歐洲對中國和日本的研究,請問有關於歐洲對於韓國、朝鮮的研究嗎?謝謝。
羅泰教授:
其實我們UCLA有一位專門研究韓國藝術的大專家剛剛退休,跟我一樣是從德國出身的。朝鮮我完全不知道。反正不能去,所以沒辦法。好像西方有一些學者可以去研究現在朝鮮的宣傳藝術。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提問:羅泰教授您好。知道您翻譯了李零教授的《楚帛書》,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研究翻譯在藝術史上有什麼意義嗎?謝謝。
羅泰教授:
我翻譯這本書的時候非常愉快,因爲這本書的內容很有意思,並且證明我們研究考古方面的題材,有時候不用自己去發掘,就是研究這個歷史的過程本身也是有點像考古般探索的方式。當然這個工作是李零教授花了很多年來做的,我僅僅是把他研究的工夫翻譯成英語。我在這個過程當中學了很多事情,原來我沒有特別敢碰《楚帛書》這個研究,因爲比較複雜,而且各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貢獻,互相之間有矛盾,不好評價。但是李零很刻苦地研究了幾十年,把事情解釋得非常漂亮,清清楚楚,把它的重要性也暴露出來。我在這本書中並沒有直接說出來,但是讓讀者很明確地感受到,這個《楚帛書》應該趕快還給中國。我後來又寫了一篇文章重複了這個觀點。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
張健教授:
最後一個問題。
陳康濤助理: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跟上一個問題有關的:請問《楚帛書》的第二冊是不是也是在翻譯當中?
羅泰教授:
是,這個我就沒有資格翻譯,因爲這是更加專門的內容。幸虧李零教授勸了芝加哥大學的Donald Harper教授做這個工作。Donald Harper在西方學術界毫無疑問是最合適擔任這個任務的,所以我們可以希望這本第二冊早點出來。工作量特別大,我估計他還在做,但是也快了。
張健教授:
好,由於時間的關係,實際上我們已經比預計的時間超過10分鐘了,我想這裡問題還有很多。羅教授您不介意再回答幾個問題的話,康濤你再接著問。
羅泰教授:
可以,我看到很多很多。
陳康濤助理:
下一個問題是:請問羅老師,西方學界有沒有研究比較基督教藝術與東方佛教藝術的成果或研究團隊?謝謝。
羅泰教授:
這個我不太清楚,可是好像Salmony當時的博士論文就是這個題目。他做日本的佛教雕塑和中世紀歐洲的雕塑的對比,之後好像還有幾個人做過,但是具體我不太清楚。這當然是在一個學科發展的初級階段,看起來比較是理所當然,要有人拿出來研究的一個題目。但是深入了以後,就會發現情況不是那麼簡單,這些類似的地方還是比較膚淺的,真正深入的話,就看起來整個都會解散了,dissolved;所以要真正循一個合理的角度去研究這個題目的話,要發展一個特別複雜的理論框架,最近可能還沒有人真正做到。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個問題是:請問羅老師,您如何看待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藝術史學建立和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學者的先驅和開拓性的貢獻?比如說第一位在柏林大學獲得藝術史博士的滕固先生,您是如何評價的?他們在民國的時代去歐洲,尤其是德國留學,對於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方法和方式產生了那些影響?謝謝。
羅泰教授:
滕固首先去了日本,然後才從日本到了德國。待著的時間不是很長,可惜死得很早,所以他的貢獻被中斷了,否則的話他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他能夠活下來,繼續做幾十年的工作,甚至如果他能夠跟當時在中國已經待著的德國藝術史家合作的話,也許就真的能夠在中國建立起研究傳統。但是很可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重慶得病死了,後來就沒有第二個在國外學了美術史回來的人,也沒有真正的發展。我可能不夠理解這個學科,我也只知道滕固。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他的問題是:謝謝羅泰老師精彩的講座,您的漢語特別棒。我有一個問題,您一開始說外國人研究中國音樂最難,藝術次之,最容易的是中國文字和哲學。我作爲一個普通中國人,其實覺得很難理解中國哲學,想請教您是怎樣去學習中國哲學的?謝謝。
羅泰教授:
這並不是我自己要學哲學的,但是看樣子好像在西方願意研究中國文學和哲學的中國專家,比起研究美術和音樂的多很多。這一點我也沒法解釋,但是也許跟Humboldt的視角(vision)有一點關係,就是說花了這麼多工夫學了語言,很多的人,尤其是首先被語言吸引的人,原先就是對語言感興趣,而語言和哲學好像也比較接近。於是既然花了這麼多學時間學這個,當然也就想在這方面多花學術工夫。我上大學的時候也是從學語言開始的,但是後來發現中國考古的重要性,而且好像西方學術界完全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所以我就被迷進去了,一直迷到現在。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想的,隆溪有沒有觀點?
張隆溪教授:
我沒有。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個問題是:老師您好,請問美國各個大學對於東方藝術的研究是不是會有不同的側重點?譬如說不同大學會對不同時段就不同媒介的東方藝術有特別的深入瞭解?
羅泰教授:
以前好像是有這個的,可是後來有一種潮流。一開始可能比較雜,哈佛的羅樾就是一方面搞早期藝術,但是一方面也要教印刷品,就是印刷藝術和繪畫好像都研究。後來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要學繪畫,當時比如普林斯頓、耶魯、伯克萊都是中國繪畫研究的大中心。現在好像看不出什麼地方特別側重某一個媒體,反正有一些大學後來加了人,像Kansas和我們UCLA,還有普林斯頓,有兩個專家。啊!普林斯頓現在已經沒有了,可是有一段時間有一個搞古代青銅器之類的,另外有一個搞佛像的,或者另外一個搞繪畫的,把這兩個分開。我們在UCLA也這樣做,我是搞考古方面的,另外我們的李慧漱教授是一位非常傑出的宋代和宋代以後繪畫的專家,我們剛好就互補長短,一起教書,非常愉快,可能這樣子最好。
可是總的來說,這當然有一點不公平的地方,我們這個系裡面搞西方藝術的同行,理所當然有好幾個。他們分得很細,第一個是古代的,我們系有兩個搞中世紀的,另外應該有文藝復興的,應該有一個Baroque,就是說17世紀、18世紀的,應該有一個19世紀的專家,還應該有好幾個近現代的,都是比較狹窄的西方的傳統,比歐洲面積還要大的中國,反而勉勉強強只有兩個;兩個就算不錯,大部分的地方只有一個。
我們的韓國專家已經退休了,現在也沒法再找新的。日本的最近又加了一個,所以我們東方藝術就三個,在美國就算非常不錯,可是總的來說這個深度還是有所差距,我們教書要教得比較廣。我一開始在我們這裡教書的時候,還沒有李慧漱教授在這裡,我就「從堯到毛」來教中國藝術史。我們說是「從堯到毛」,從新石器時代甚至舊石器時代一直到20世紀,當時還不是21世紀。西方藝術史的老師,叫他從Plato教到Nato,他就會拒絕,他說他只要教他的這一段。小的學校,像比如說4年的college,當然是這樣講的。整個美術史系可能只有兩個教授,一個是搞西方的,從Plato到Nato,另外一個做非西方的,可能是一個非洲專家,但是非洲專家也要教日本和中國。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個問題,這位來賓想請教羅泰教授和張隆溪教授,就是內地許多藝術史的研究偏重考據學、文獻學,而國外的藝術史研究許多methodology是從人類學、社會學裡面借鑒的。很多人認爲國內的研究多數是考證出來一個事實,可能過於單薄;也有很多學者認爲外國學者比較多用概念。關於中外治學的差異和共同性,想請教兩位老師怎麼看?
羅泰教授:
我先說一句,麻煩的剛好就在那裡,考據學之類的、文獻學,雖然能夠用來研究藝術品,但是這還不是藝術史。嚴格意義的藝術史是瞭解,就是verstehen,瞭解某一個時期或者某一個藝術家的視覺方式、表現方式,還有visual conventions,就是它怎麼把外界通過這個視覺的媒體翻譯成一個藝術品的過程。在這個研究裡面,考據學之類的,就是還有讀銘文之類的,這些都重要,但是僅僅是一個初級階段,不是它的本質。很多自稱研究美術史的人不明白這一點,不明白美術史內在有一套主題思想,這個主題思想還沒有被他們接近。這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現在在我們這裡也有,有一些人就是像剛才問題所說,他以爲我們這裡是從社會學、從人類學的角度搞美術史。對,可以用這些方法,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方法,但是這還不是藝術史,這僅僅是輔助的一些方式,可以瞭解外圍的一些情況。核心的理解是另外一套,跟哲學和歷史學比較接近。
張健教授:
這回最後一個問題。
陳康濤助理:
羅泰教授您好,有學者認爲藝術史處理的是特殊性的問題,考古學處理的是普遍性的問題。請問您怎麼看待藝術史跟考古學這兩個學科之間的關係?
羅泰教授: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基本上我這一輩子都一直做藝術史教授,但是我並沒有專門學過藝術史。我上過課,但是沒有受過藝術史的訓練。考古呢,在我的訓練當中是人類學的一部分,是一個社會科學,是研究古代的社會發展過程,但是其實考古學還有很多其他的層面,是一個多學科的探索方式,也可以包容藝術史,或者藝術史也可以包容考古的資料,但是藝術史本身的方法論,和考古是分開的,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你研究classical archaeology,就是希臘羅馬的考古學,它裡面有一個分支,其實完全是藝術史的研究,但是我一直感覺這種對希臘羅馬文明的遺物研究被錯誤地放在考古系裡面,應該放在藝術史系裡。現在的希臘羅馬考古,雖然還有一些學者採取這個觀點,尤其是在德國,但是主流可能偏重於文化和社會體系發展史的研究方法,就是把大量的物質文化,不只是藝術品,而是把各方面的物質文化當作歷史材料。這個方法跟藝術史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
張健教授:
好。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不得不到這裡結束。這是一次視野極其廣闊的講座,討論的範圍遠遠超出了東亞藝術史,超出了藝術史,對於我們思考文學、音樂、書法、文化……這些範圍廣闊的問題,我想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相信會引發大家的思考,所以我們的講座是結束了,但是思考剛剛開始。我們會把講座的視頻,還有整理出來的文字稿,將來在徵得羅教授和張教授的同意之後,公佈出來,大家可以再繼續留意。我們再一次感謝羅泰教授,感謝張隆溪教授,也感謝在線的各位朋友,最後也要感謝我們這次講座的各位助理。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謝謝。
羅泰教授:
謝謝,希望能夠早一點真正的見面。
張健教授:
對,希望有機會請您來香港現場講座。
羅泰教授:
或者歡迎你們再到洛杉磯來。
張健教授:
謝謝,好,再見。
講座錄影
系列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中心(JRCCLAL)舉辦,講座視頻已在YouTube及bilibili影片分享網站發佈,可以點擊相關鏈接觀看。
本中心主辦「漢學講座」系列
第一講:「美國漢學五十年」
主講嘉賓:艾朗諾教授 陳毓賢先生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N411f7pi/
YouTube: https://youtu.be/6nyJaYZFoV0
第二講:「東亞藝術史研究在歐洲的源流和發展」
主講嘉賓:羅泰 教授 對談嘉賓:張隆溪教授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V411p79n/
YouTube: https://youtu.be/ua8Gmy8GCW0
本中心主辦「人文講座」系列
第一講:「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
主講嘉賓:張隆溪教授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h41127zk/
YouTube: https://youtu.be/e4J853XeBYU
視頻剪輯:邱嘉耀
講座助理:陳康濤、陶冉、許鑫輝
圖文版權:由講者提供,版權爲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