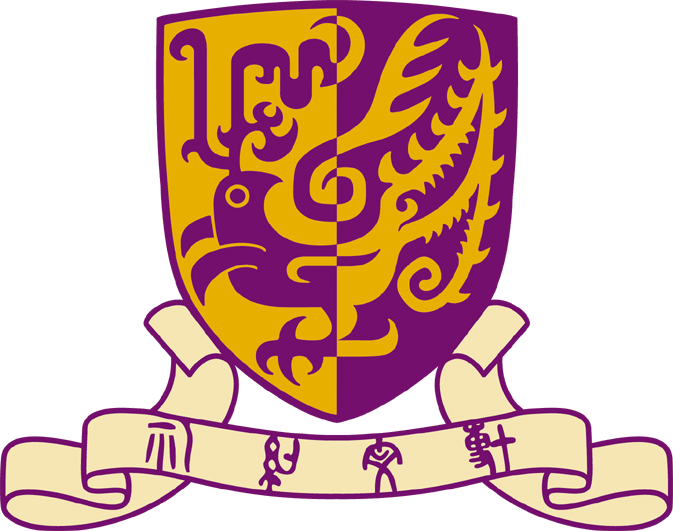本來我是想讀社會學,結果行錯路去了人類學系那層——大部分中學生如我都不知道這科,總覺得好多讀人類學的人都是蕩失路、撞上去,卻發現它比其他學科更有魅力、神秘——從前的人類學家研究原始部落文化。
大學時什麼都八掛,take了譚少薇教授關於性別研究的科目,算是對性別問題有最初步、理論層面的接觸。後來發現性/別議題很貼身、日常:你能見到摸到、強烈感受到,作為一個人,不論性別與性取向,如何受「正常的社會標準」制約、形塑和壓迫。後來任職記者,就夜蒲、約炮等兩性文化訪問過鄭詩靈教授,由人類學的角度討論性別議題。
大學時已有在雜誌社實習,挪用一點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寫過清潔工、貧窮人口等題目,其後也有為性工作者團體做人物訪問。想做記者,因為我對人的故事有濃厚的興趣——我知道這聽來好空泛、好廢。我並不是理論性很強的人,也抗拒什麼「主義者」的自稱;記者的身位則很適切。好多人對記者有一種奇怪的信任感,會邀請你進入他/她的秘密和心結裡頭。
人們對某些群體、族群往往有根深柢固的想像和偏見;讀人類學,讓我很早卸下這種認知世界的方式。這對記者做訪問、切入題目很有幫助——有些發問的方式透露出你的偏見和既定立場,像監控的一種,令對方不願意講出事實或心中所想。另外,讀過人類學的記者訪問和寫作模式、關心的議題或許也有點不一樣,會更加重視個體,甚至小眾的聲音,不是把人歸納為統計數字,而是以小見大地去講社會現象。細心聆聽、摒棄成見、發掘問題的核心,都是靠人類學的學科訓練。
聘請我的主編,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覺得人類學背景是優勢的雇主;她知道人類學是什麼,好多香港雇主都不知道;解釋完是一臉不解,似乎聽不出有什麼技能。我總覺得人類學家對社會好重要,但在香港感受不到……
我在現職媒體加入的是Well-being組,探討題目廣泛,性愛、性別是其中範疇。也許因為受過一點相關訓練,我不怕和「性」連上關係,而別人怕被標籤,自然地,這方面的題目我做得比較多。做記者,感覺掌握了一種傳播工具;現時網媒講求數據,更見傳播的痕跡。但是,我現在做的,距離倡議和社會運動,還超級遠;單憑網絡媒介的單向、海量、瑣碎且娛樂化的傳播,不足以「運動」到什麼。(然而我相信其他記者有更好的方法在做。)現在工作的影響只在於讓議題「被看見」,微小力弱地建構別人腦袋裡的一些意識,這是「傳播」的功能。
一方面覺得自己做的報導有點意思,同時又覺得沒有意義:現時所有事物被消耗的速度都在加快,性是網絡上吸引眼球的題材;你不知道性議題是被看見,還是因為夠爆夠聲色,因而更被即用即棄?這類報導有點像同時也蒙受著這議題的「汙名」。 於是每天都在掙扎之中,經常感覺迷失和不知所措。網民需要消耗的東西,和我在現實生活中經驗到的,很分裂。似乎大眾生活得越苦、越無力,就消費越多與自己無關的「想像」,而我們就負責製作和包裝那些所謂美好的「想像」,大家一齊被推著走。有時寧願不思考,故意催眠自己,只著眼於自己可以做到的部份。或者要真正離開了那loop, 才有空間思考。
無論如何,「性」都是香港社會需要繼續討論的題目。後期,我想從「小眾」、「邊緣」抽出來,談多點普通人的性愛、性別角色以及更集體的困難(如性空間、無性夫婦、秘密的性關係、處女新娘和性知識等等),令整個議題不再是旁觀別人,「獵奇」別人。 有時喜歡和沒有經過性/別意識訓練的女仔做訪問,好像更見到問題所在。她們沒有受過性別意識的訓練,但又真正在實踐情慾自主這件事。當要講她們的情慾經驗又是怎樣?能自主到什麼地步?原來有不同程度的包袱,包括如何平衝形象和欲望:當她們想行拍拖結婚生仔的線性人生,她們又要面對什麼目光?她們似是開放,但狀態都是地下,不可以講出來,在香港,甚至可能有懲罰、受非議。你都可以說她們是「邊緣」、「地下」,但其實不過是普通人,像你我般被模塑。
一寫性好似停不下來。一年半前第一篇講「如何做好一場愛」,做到現在討論性暴力、陰道獨白,好多informant跟我談他們的性故事,一塊塊碎片砌出比較完整的畫面。因為坊間絕少有性方面的討論,一開始我沒有組織性,跟著網絡閱讀習慣和關注點、還有自己的觀察去寫。漸漸發現原來所有題目環環相扣,覺得像做一個「港式性事」的「田野考察」。但一路圍繞一種題材做,难免重重覆覆,每次覺得做到油盡燈枯時就問,還有沒有新的題目?還能不能發掘新的角度?怎樣討論才不學究,將「性」還原為人的本質問題?香港地,還找得到人肯公開談性嗎?
(圖為余婉蘭訪問變妝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