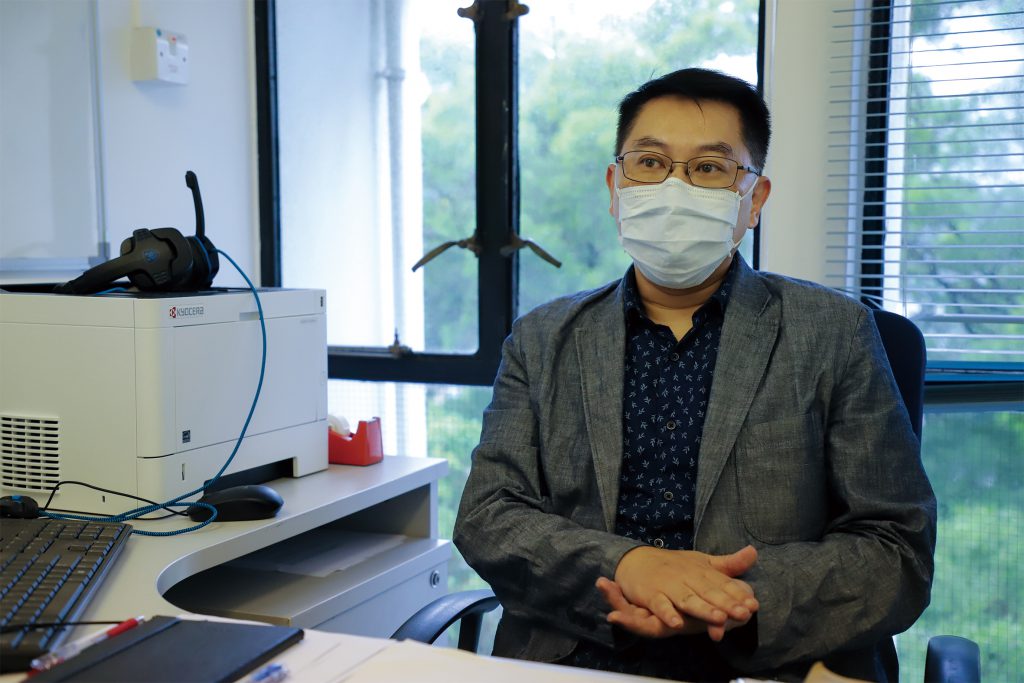「我雖然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出門沒有健康碼,就像做賊一樣。」沒有健康碼的北京居民楊勇(化名)慨嘆。楊勇疫情前幾乎天天外出工作,但由於一直沒有申請健康碼,近半年來,他寧可窩在家中,每天在電腦上辦公和娛樂,三餐依賴外送食材,過著平均每月只出門兩次的生活。
二月初起,內地各省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推出健康碼政策,規定市民出入公共場所時,包括商場、地鐵站、辦公室等,都必須提供綠色健康碼,證明自己「健康」。無可否認,健康碼有助追蹤確診個案,令不少人安心;但另一邊廂,健康碼為出行添上不少麻煩,更有市民擔心會被侵犯私隱。
記者|林踔賢 編輯|盧文樂 攝影|林踔賢 盧文樂
北京政府在三月上旬推出「北京健康寶」,但基於私隱考慮,30歲的自由工作者楊勇至今仍沒有申請,一直以來都盡可能不踏出家門,日常生活所需都靠快遞解決。若果必須外出,他會選擇駕車,以避開任何要出示健康碼的場所。他承認,沒有健康碼對他的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在內地生活,早已不能避開各種追蹤程式。楊勇認為,政府可從微信、支付寶等需經實名認證的程式中,精準地掌握每個人的行蹤。他一直對它們的安全程度有所顧忌,習慣關掉定位系統。他更不願因為健康碼,再向平台提供額外的個人資訊。而他抗拒健康碼最主要的原因,是該程式必須通過人臉識別,他不清楚政府收集人臉特徵的目的:
「人最恐怖的事情不是已知的東西,永遠是未知的。」
對他而言,人的臉龐與電話不同,前者不可能輕易更改,因此不能隨便提供予第三方機構。他亦不明白為何健康碼必須通過人臉識別,認為即使撇除功能,也不會影響運作。
外出經重重關卡 心情如「做賊」
六月初,北京疫情曾一度放緩,政府繼而將「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由二級下調至三級,並放寬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進入小區前的探測體溫要求。眼見政府措施開始鬆懈,楊勇在六月中便約同數名好友,一同驅車前往北京近郊的寓所聚會。
可是,在短短數日的休假期間,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爆發新一波疫情,政府又隨即上調應急響應至二級。回程時,楊勇十分緊張,因北京道路長年設有不少檢查站,工作人員會檢查車上人員的身分證、車廂和車尾箱,他擔心在防控等級上升後,政府會推出新措施,加派防疫人員檢查往來人士的健康碼,或甚是強迫他即場登記健康碼。即使檢查站職員最後只檢查了車上人員的身分證,楊勇仍然心有餘悸,感覺自己就如偷渡客:
「我雖然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出門沒有健康碼,就像做賊一樣。」
維權律師斥欠私隱 「未有異常」非易事
維權律師包龍軍長居北京,疫情前常因公務到處奔波,連續一周不在家是平常事。健康碼推出後,他儘管擔心程式會蒐集個人信息,但因為有時不得不外出辦事,所以健康碼是非裝不可。他已經盡量減少出行次數,即使要外出購物,都會捨棄便利的大型商場,選擇到小型超市或市場等毋須使用健康碼的地方。
他認為,微信已能做到實時追蹤,而且國內各種各樣的監控無所不在,但健康碼清晰列出用戶途經的地點,使監控變得更加嚴密,更加可怕。包並不喜歡被人實時監控,而作為身分敏感人士,他認為健康碼不只針對他們,更將監控範圍擴展至所有普通市民:
「像我們這些在這國家已經沒有任何隱私的人,倒不是怕這個東西,就是我討厭這種做法,這種未經我同意,強行加給我的一種霸凌。」
除了面對實時監控,包龍軍在使用健康碼時亦常遇困難,其中一次發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九月初,他要到成都出差,但卻一直滯留在機場外,未能成功通行。他憶述每次進入首都機場前,必須在「防疫健康信息碼」申報過去14日的行蹤,結果要顯示「未有異常」才能通行。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因為程式後台記錄每日行蹤,所以登記人士必須準確申報所有到訪過的縣級市,一個都不能少。由於他剛從內蒙古回京,回程時乘搭的火車沿途經過不少城市,他不肯定是否因系統誤會他曾到訪多地,才使他屢試屢敗,但當時又申訴無門,使他非常著急。
擾攘半個多小時後,工作人員見他實在沒辦法,才叫他以紙筆登記個人資料,方能進入機場,耽誤了不少時間。他又提到,每次到高鐵站和機場等場所,門外總有不少人埋頭在手機上輸入資料,和排隊等候掃碼。為免阻礙行程,他都會比以往提早半小時出發。

有別於內地其他健康碼,「北京健康碼 」會同時展示出用戶的樣貌及身分信息。(受訪者提供) 
「防疫健康信息碼」要求用戶申報14天內在國內停留四小時以上的城市,其後後台會通過電 訊營運商提供的信息核實,包龍軍多次提交失敗。(受訪者提供)
商家地級市各設碼 碼上加碼非互認
港人陳瑩(化名)任職中國組記者三年多,在八月,上司安排她到浙江工作。她本以為持著浙江健康碼便能在省內通行,豈料當她打算進入當地一個商場採訪時,卻首次遇到職員要求她額外登記由商場自行創立的健康碼,作雙重認證。除了憂慮要提交個人資料給未知的第三方外,陳瑩亦發現當中的審批過程極不透明。她觀察到身旁的內地市民只用了數分鐘,便成功註冊,進入商場;但她在現場等了近一小時也未能辦妥,甚至在完成當地三天的採訪工作後,依然未通過審批,最終只好放棄到該處採訪。當時,她曾嘗試詢問商場職員未通過審批的原因,但他們也未能解釋,只叫她耐心等候,令她懷疑某些健康碼對港澳台人士審批較嚴格,令人無所適從。陳對未能進行預期的採訪表示可惜,因為缺少了一個如實反映當地情況的機會。
來自吉林省、現正在港就讀碩士課程的曹同學亦有類似經歷。六月底,他趁著疫情放緩,前往河南遊玩。由於他要先到內蒙古烏蘭浩特及黑龍江哈爾濱轉機,於是短短一天內,他便分別申請了三地的健康碼,申請亦非次次順利。每次上機前需要先申請好目的地的健康碼,但在內蒙古轉機時,系統要求他填寫到訪黑龍江的目的、到訪住址及預計停留時間等。在「目的」一欄,卻唯獨沒有「轉機」這選項,於是他向工作人員查詢,但得到的回應是叫他「亂填」,令他覺得設計不夠完善,未能涵蓋所有出行需要。而在河南省旅遊時,當他由鄭州坐高鐵,到屬同一省份的開封市時,當地又要求他註冊屬於開封市的健康碼,不能以河南省健康碼代替,就算申請手續不算繁複,但他不明白為何兩碼不可互通,認為是多此一舉。
大數據時代 如何才能運用得宜?
在內地,手持健康碼出行已成「新常態」。九月時,蘇州在健康碼系統「蘇城碼」上,新增「文明碼」功能,就市民遵守交通規則和參與義務工作兩方面評分,但推出一周後便受到多方批評,指過度干預個人生活,在怨聲載道之中下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認為,數據監察在多國都有廣泛應用,也不否定收集數據有助控制疫情,但在中國卻變為少有的數據獨裁(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他指出,內地健康碼運作欠缺透明度,行政和立法機關亦缺乏制衡,市民難以監察政府有否濫用或誤用數據。他又強調,「資訊就是權力」,在數據管治的社會裏,要令市民願意交出數據,前提是市民與政府要有互相監察的機制,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對等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市民)提供數據給你(政府),那麼我都要監察你如何運用數據。」
針對省市各設健康碼的亂象,黃偉豪認為問題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使全國在使用健康碼上的立場統一,但真正實施權力的是地方政府,不同地方政府套用的健康標準不一,導致健康碼在操作上並非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