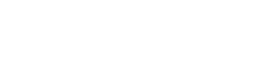吾生有杏:院長醫生周記(五十)諾貝爾獎有感
本年度的各個諾貝爾獎項陸續揭盅了。我們的盧煜明教授是熱門人選之一,不止中大人,整個香港都感到十分興奮雀躍。此外,日本科學家連續三屆奪得此項殊榮,世人驚嘆他們卓越的成就之餘,我也不禁想:「香港可以栽培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嗎?」
不少人批評香港教育缺乏長遠策畧,社會出路越來越狹窄,令年青人流於現實,不願追求理想,所以大部分成績優異的學生都蜂擁選擇讀醫、法律、金融等前途光明的專業。
我從事醫學教育多年,其間接觸過不少對科研或人道救援充滿熱誠的年青人。在我眼中,他們都是「另類」。因為大部份醫學生的志願都是畢業後從事臨床工作,選擇像盧煜明教授般成為醫生科學家 (clinician-scientist) ,或仿效校友陳健華醫生加入無國界醫生參與人道救援的,畢竟是少數。事實上,有熱誠有潛質的同學為數不少,但這些學生往往經不起來自周邊的壓力和中途遇上的困難而最終放棄。為甚麼?
以科研為例,雖然香港的醫學研究享負盛名,但科研對一個前綫醫生的前途沒有甚麼幫助。這些年青人往往因為要額外花上幾年時間鑽研科學而躭擱了畢業後的專科訓練,擁有醫學博士學位的醫生亦不會比其他人有任何優勢。高學歷不會增加將來晉升的機會,變相窒礙了年青醫生追求科研的熱情。
反之,在日本、台灣及荷蘭等地,醫生必須擁有科研經驗或博士學位才可於大醫院找到工作。這些醫療體系鼓勵醫生從事科研,亦因此解釋為何他們的科研成就驕人。
在香港,於教學醫院工作的醫管局醫生要同時兼顧教學和臨床服務,工作量比其他醫院更重。在人手及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教學醫院工作的前綫醫生根本無暇投放精神在科研和創新醫療科技上。
我看到的問題是,如果醫學教育祗着重培訓人手去補充公營市場的需要,而科研被視為一種「負擔」的話,香港的醫學研究和整體發展將無以為繼。沒有與時並進的醫療科技,最終受累的,是市民和病患。
我看,是時候改變了!
要改變醫療制度或價值觀,談何容易?但我們必須為着香港的長遠發展締造一個更全面的人才培訓方案,為懷抱不同埋想的年青人打造一個合適的環境和條件,讓他們一展所長。例如我們應考慮容許某些科研或人道救援的經驗替代部份專科訓練,以鼓勵更多年青醫生參與。宅心仁厚的醫生和改變世界的醫生科學家對人類同樣重要,缺一不可。「人」最特別和珍貴的地方,就是每個都不盡相同。發掘他們的獨特之處,然後「因材施教」,是使命、也是目標。
我信,出產到「香港製造」的諾貝爾獎得主並不是發白日夢或「離地」。香港的孩子天資聰穎、擁有國際視野,他們絕對有能力在科研、人文科學或人道救援工作的領域上貢獻人類,讓世界變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