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本長紀錄】《民現》新書發佈講座
文//李薇婷
時間:2020年6月2日
彭:彭麗君/譚:譚以諾/張:張可森/梁:梁寶山/李:李祖喬
整理、記錄:李薇婷
紀錄按:問答環節以私隱為由,以聽眾A、B、C的方法紀錄提問者。
政治現場與政治理想:阿倫特作為方法
彭:這本書的理論部份主要和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1906-1975) 對話。身為一位原籍德國的美籍猶太裔的學者,阿倫特是個有趣的人。她首先是德國猶太裔思想家華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好朋友和研究者。同樣是猶太裔的思想家,本雅明最後死在德國,但阿倫特成功逃離,若不是她,本雅明不會在五十年代後為全球思想界所熟悉。而阿倫特在離開德國遊歷於不同地方,之前之後也一直問:所謂「德國人」、「猶太人」,究竟是怎樣的群體。另一方面,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組成者大部份是德國猶太裔的離散學者,但在這群思想家當中,背負這許多種族、學術背景的阿倫特,卻與他們的思路明顯不同。再者,她雖是女性,卻從不願意被標籤為女性主義者,甚至於八十年代受到許多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她研究的許多題目均沒有從體諒女性的視角出發。但到了最後,儘管她背負的是整個德國哲學的傳統,總是從古希臘尋找資源來談論各種問題,但是,她卻不認同哲學家的身份,走進政治研究。凡此種種,加上她雖然經歷猶太苦難卻拒絕作猶太人的代言,再回過頭來提問,究竟整個歐洲哲學傳統背負怎樣的問題,她甚至認為納粹主義的生成必須從西歐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發展而理解,是西方文化的衍生物。她對此的反省態度非常強烈,甚至對猶太人本身的批評亦極為深刻。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吸引的,她可以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同時亦很貼地般提問政治是什麼、「參與式民主」為何、人如何作政治參與和日常實踐。我認為思考這些問題都能幫助我們離開現時的困頓。
 漢娜‧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
譚:除了與阿倫特對話,你在書的緒論亦提到「共居」。你如何透過此概念理解雨傘佔領區的民眾呢?
彭:「共居」對應兩個層面。一是傘運佔領區當時屬於眾人共同居住的狀態。雖然後來許多民眾可以隨意進出區內不同的帳幕,漸漸也沒有太多人留居,但整體而言,佔領區仍然是個「共居」的狀態。這種示威模式,以全球佔領為參照,是一種很對應當時社會狀態的示威模式。另一方面亦要回到阿倫特的理論。阿倫特其中一個理論框架是「私人-社會-政治」的三元關係,私人是各種不曝光的私密行為,包括個人感情、家庭、吃喝睡之類、最貼身的感情流通之地;社會的層次則是漸次強大的現代社會,人們日常生活、工作、和他人建立關係的空間;對阿倫特而言最重要的空間是政治空間,亦即是「現身空間」 (the space of appearance)。這空間由一群人放下自己的個人利益與感情,進入現身空間進行政治活動。這空間是從希臘的政治哲學中引申出來,很理想化。這空間擁有多元性,每個個人進入此空間都帶有他們自身的背景。但這並不是什麼大愛左膠空間,反而因為人人都帶有個人訴求進入此空間發聲,所以,這空間內有許多不同意見。這是個平等的空間,不是因為大家都一樣,而是因為沒有任何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權力,大家都可以提倡自己的想法。這是很理想的自由空間──這「自由」不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自由」,也不是消極自由 (negative liberty) 的「自由」。這裡的「自由」是指,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空間進行自己要做的事之時,並無特權要控制他人做某件事。其實許多時人們發聲時都希望說服他人聽自己的話、跟自己的主張行事,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能控制他人跟隨自己的想法,當中可能一事無成,也可能成就大改變。你或者會說,「啊,這真是不自由的,因為我們做每一件事都好像要受制他人」,但是,當這種平等的狀態同時亦導致無任何人可以控制結果。阿倫特所言的政治自由,其實是非工具性的自由。當我們可以放開功能性的自由,就可以做到更高層次既自由個體,達至政治自由。我認為現時香港民間有這樣的面向。試想像,有一千甚至一萬人,愈來愈多人攜同不同的目的進入抗爭現場時,愈是無人能夠控制結果,但當你面對無法控制結果的局面,仍然願意為自己的理想而繼續爭取,就是政治最理想的狀態。「共居」基本上就是從這些層次來展開的思考。
譚:這是個很宏觀的話題。聽到你的解釋後,我所理解的是,雨傘到反修例運動的狀態,同樣是幾千幾百萬人在同一個空間裡發表意見。當中出現許多拉扯、協商,亦因為無人可為他人作決定的原故衍生許多張力,甚至是停滯的狀態。我相信這是大家在雨傘時期的共同經歷。金鐘、旺角佔領區中後期所出現的停滯、甚至爭論、抹黑,令我思考,共居是否一定走向停滯的狀態?抑或能提供一些正面的力量,讓大家解決到當下的問題?
彭:有的,這本書的另一對應正是這種停滯感。特別是第四、第五章寫藝術和紀錄片,我很感動於大家把面對停滯、等待時亟欲做些事卻又無能為力的煩厭感覺,轉化成拍紀錄片、甚至索性在街頭打場乒乓球的行為。就像是世界不受控制,人們卻自覺必須參與。其實直至今時今日,我們同樣面對這種眾謂「無力感」的狀態,相當真實──既無法控制現實,而就算能控制,最終亦未必是大眾想達成的理想。特別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的確是一場反極權運動──我並不想定義現在的中國是否極權國,因為不同的理論家對「極權」都有嚴謹的介定,中國不一定能夠符合這些定義──但是,儘管中國未必能稱為極權政府,但反修例運動的確是在反抗「極權」這種狀態。面對「極權」這種講求「絕對的整體」的狀態,人民的抵抗與回應是什麼?我認為我們正以多元的、自由的,甚至是一種等待的狀態來回應「極權」所依靠的單一邏輯。另一項值得我們繼續想像的是,阿倫特企圖處理多元的政治狀態,這與德國另一個政治理論家史密特 (Carl Schmitt) 的敵友關係很不一樣。他在1920年代時認為當時的德國已經去政治化,大眾忘記了什麼是政治,而政治最基本的狀態便是敵友關係。施密特的思考可能很有啟發性,但這只是其中一種思考政治的方法。阿倫特便以多元來思考政治,儘管她經歷過納粹集中營這種極權統治。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用哪種方式來回應極權?以對方所應用的敵友原則,抑或多元關係?我覺得應該要更仔細思考。
 Credit: Gregor Klar
Credit: Gregor Klar
從香港到全球:「城市權」的理論與實踐
譚:我最後一道問題:您書中提到「城市權」,當我地用城市權來談論香港反極權運動的狀態,究竟意味著什麼?如何對應香港從雨傘到反修例運動的處境?
彭:以「城市權」來談論香港有幾個原因。首先,香港本身是城市,大家討論民主的時候多用「民主國家」的進路,我希望思考「民主城市」。除非我們不談民主,要談民主便先要理解,民主沒有一條必然的路徑,它可能是一個終結,但這個彼岸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民主也是一個存在許多內部矛盾的政治概念。這意味我們要香港達至民主,不能說參考台灣、南韓怎樣做,我們便跟隨之。反而,我們要回到香港的身世,它是城市,從未真正自治,卻總是處於半自治狀態的政治實體。所以我在第六章中提過這百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的三種狀態。一是城邦,在許多不同帝國之間尋求生存方式;二是全球城市,許多資本從香港通過,使香港變成世界中心;三是難民城市,因為香港人口一直由不同的難民群體來組成。我認為大家要理解這三種狀態,學懂欣賞自身的優點甚至包袱。這種對城市形態的認知,可回到我在引言部份談論過的「眾多主權」。寫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理想,就是把香港的問題和世界的問題聯繫起來,國家主權是一個當代很重要的問題,香港的狀態可以作為一個想象方法去處理一些其它地區的問題。主權這個概念似乎包含一種高度統一性的權利,不能分割,但我們可否拆解這種迷思,在主權中同時處理統一和多元的矛盾?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擁有主權,但國家之間有很多誇國的主權操作,在國家之下的各地方亦有地區主權,甚至是社群 (communities) 為單位所展現的主權。在此狀態下反思香港的「高度自治」又將如何?我不想,也沒有能力為香港提出治港藍圖,我只是希望提出的想象的可能。
譚:謝謝麗君老師的分享。落入城市權這個議題,我想新近成為區議員的張可森可以分享一些基於議員身份所體會到的、一般市民不瞭解的城市經歷。作為前線實踐的一員,你如何理解和回應「城市權」?
張:我認為「城市權」的概念很能回應眼下香港的狀況,引發我思考香港如何走下去。我從搶白區行動成為素人區議員,如何回應國安法、思考香港前途對我來說都是最逼切的議題。「城市權」可以從陳雲提倡的城邦論談起,不過,他口中的香港城邦是承傳華夏文化的地方,但《民現》中提出的城市權,其實認為城邦不一定要講求「華夏傳承」。從地理概念上思考,中國可以說是以陸地模式來思考,認為香港是帝國邊垂的空間。但是,從海洋模式來思考,香港便不是邊陲。何以在此時以「陸地-海洋」來思考香港呢?因為陸地是一種以國族國家邊界作為中心的思考,但海洋的邊界卻是模糊的、流動的。從海洋模式來看,香港才是各種流向、包括資本流 (capital flow) 的交匯點,我認為這是中港之間最大的分別。捉緊這點模糊的邊界,回到「自由」這一個支撐著本地抗爭的重要概念,我認為一個城市的開放邊界是很重要的。只是,要強調的是,不像某種本土論述認為開放邊界會令香港淪為內地大媽等外來文化入侵的地方,我認為開放邊界最重要的不是有什麼人進入香港這空間,而是香港如何回應這些外來物。城市會開放邊界,同時亦會回應進內的事物。例如Pepe本來亦是從西歐的網絡文化而來,但是,香港的抗爭者將之轉化成屬於香港的自由、抗爭的象徵物,甚至令原創作者形容香港人令pepe甦生。這就像歷史中的香港,是否從來都習慣以內在的轉化來回應外來的所謂「入侵」?這正是海洋城市的特質。當然,我對城市權亦有疑問:我們是否過度以「香港中心」來思考香港?那些與我們一同生活卻不屬於「城市」空間的民眾又如何?我仍未想清楚。只是,我很關心城市的位置,因為城市權的提出似乎可以回應我們很希望打破國族國家的體制的訴求,除了香港能取回自己失去的權力之外,同時能否從香港反修例運動經驗中提煉一些元素來回應全球語境?另一點我想回應的是,《民現》一書中提到「發展共同體」與「反發展共同體」之間的過渡。香港的上一代以「發展」作為推動共同體的思想價值,但下一代卻有一種「反發展」的訴求,希望保育香港,例如保育天星、皇后碼頭、菜園村等。我想再提出另一種共同體,由一種情感主導式的共同體意識,對香港有一種情動力(affective)的依歸,有點類似梁繼平所提出的「苦難的共同體」。
除此之外,麗君老師剛剛提到她的書不像陳雲一樣要提出藍圖計劃。不過,從實踐的方向而言,我感覺到現時從政者、區議員們其實漸漸繪畫出藍圖。例如像攬炒巴提到的,結合388位區議員來組成一個像「下議院」形式的機制呢?坦白說,我本人對於區議會在架構上的功能存疑,再加上香港政府仍然在以不同方式來局限區議會功能,民政官員甚至要求區議會議程只能談論種不種樹、是否建成新燈柱等他們意義下的民生福利議題。但是,我們與市民都不希望區議員的功能只止於此。除此之外,國安法實施之後,大家對選舉的期望已經很微弱,但是,我仍覺得初選好重要。假如大家以為初選只是選五位心水議員來參與立法會選舉,是小看了初選的意義。事實上,初選是五區、超區連結起來的,首次由香港人親自舉行、參與的全民選舉。假如要談論「城市權」,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城市權以怎樣的模式實現?眼下我們能否從現有的模式中提煉出新的方向?我認為這是需要更多嘗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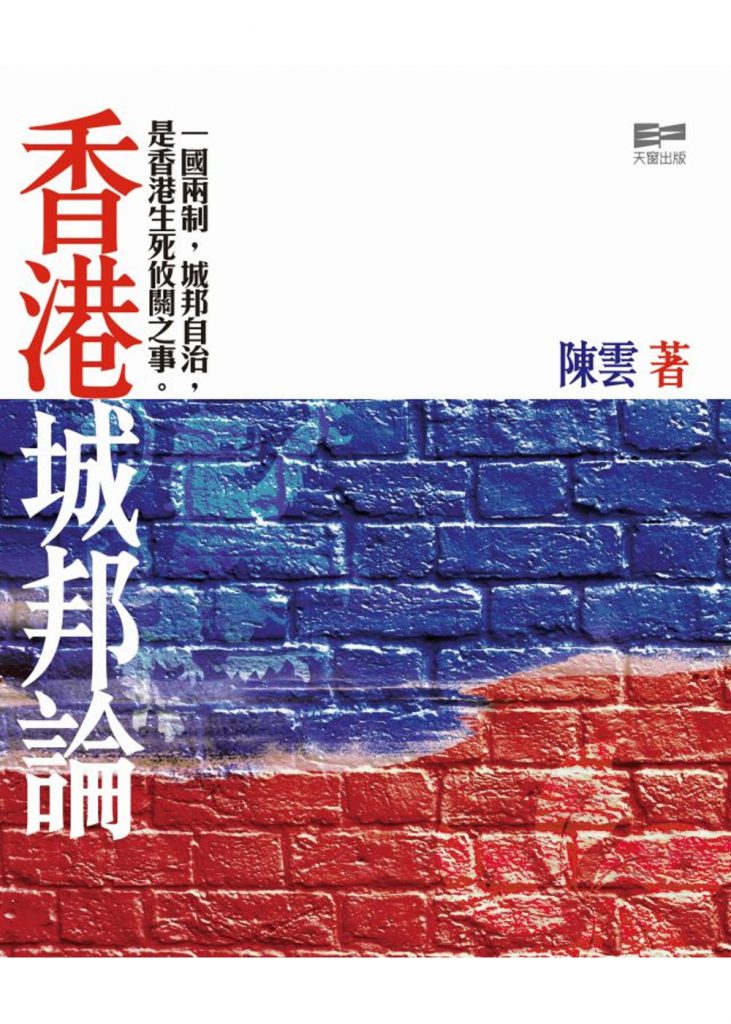
譚:可森談論的其實是關於國族主義的問題,亦是《民現》一書有回應的一點。書中另外有提到聯合國 (super national) 的層次的組成,也有次主權、次國家 (sub-national) 的組織體系。然而,這種架構體系真正出現的話究竟是怎樣的形態、如何運作呢?如果以可森或者攬炒巴的說法,似乎香港與世界可以是一種非國族基礎的連結。我想追問關於這388位區議員之間的連結,你如何理解區議員與城市權的關係?城市又在「城市權」的概念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張:我想解釋,388個區議員是投票結果,但我提倡的連結形式是透過公開邀請18區區議員一起舉行會議來建立共同議政的狀態。區議會成為直選所得的、簡單多數的議會,成為更仔細地反映香港公民意見的議會。如果這種跨區連結成真,民選代議士能做到的工作便更多,例如議決與其他城市締結為姐妹城市、聯盟等決策。我想思考的是,香港是否能以這種形式加入全球城市的行列?
政治與藝術:藝術開啟的多元政治思考
譚:這確是宏大的藍圖。梁寶山說她希望全面地談論這本書,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她。
梁:我想回應剛才張可森提到「海洋-陸地」的思考模式,為何會以「陸地中心」的模式來思考國家呢?這問題與我最想分享此書的第四章有關。我希望從一個藝評人的角度與兩位對話。談及陸地與海洋,我聯想到幾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也聯繫到藝術為何能參與這場對話。楊嘉輝 (Samson Young) 有件作品題目叫Liquid Borders,概念是他沿邊境的鐵絲網收音,和作視覺田野紀錄──聲音和流水會有邊界嗎?鐵絲網作為一個發音的物體,以及藝術家所身處的地方亦成為他收音的空間。當時正值中港矛盾、民間反蝗很激烈的時刻。但是,當他以聲音作為媒介時,所謂邊界的問題是不存在的。聲音是看不見的,但卻不停在邊界與邊界之間游走,正能回應我們現時對邊界的思考。另一個我想談論的作品是蕭偉恆在大概三年前進行的「InsideOutland/境內景外」,以影像的方式來製作。這是一個關於「東方之珠」的神話,他所拍攝的大鵬灣,歷來是偷渡之地。當時人們常說,偷渡時向有光的地方游,便是香港。(唐書璇《再見中國》1972)。然而今日在下白泥、尖鼻咀、網井圍,經過多年來資本高速發展,深圳才是光芒所在。這兩個作品,都讓我們反思「邊界」究竟為何?是國土分野,抑或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分別?
 蕭偉恆「InsideOutland/境內景外」
蕭偉恆「InsideOutland/境內景外」
另一個我想回應的是「城市權」。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思考模式會否邊緣化其他群體呢?我想另外分享兩個作品來回應。首先是盧建民在攝影節展覽的作品。他與梁天琦同期被判刑。盧建民喜歡行山,也愛拍照,這些照片的視覺是從香港不同的高山上回望城市,與我們刻板地以為香港就是維港、高樓大廈不同,他的香港是高山,例如從飛鵝山俯拍東九龍,穿插這些年抗爭者的照片。這種強烈對比,令我重新思考香港的地景。最後,我最近在進行正在研究自己居住的離島社區風貌,與港九新界相當不同。這二十年來我看著每逢打風時海邊水位愈漲愈高,沿岸的土地不斷被水侵食。海洋的力量令我有許多體會。離島有高度的族群流動性與開放性,與我們所認識的新界族群的落地生根的感覺不同。離島居民包括本地搬遷的、行船的、外籍人士;也有不同的家族形式,香港可能只是他在世上的基本家園,在外國又有第二家園。由離島來看香港與世界的關係,便不止於高度資本流動的國際都市的關係,而是有多重層次的關係。
《民現》的第四章談論佔領區的藝術展現,這一章非常點題。究竟人們是如何出現於佔領區?過往我們談論政治與藝術,往往認為兩者之關係,就是用藝術反映政治現況,但佔領區的藝術概念恰巧倒轉──是藝術展現,這些客體,令人們對城市、對政治有耳目一新的理解。藝術的作用其實就是如此。麗君以阿倫特反思香港,其實阿倫特對藝術的思考很「康德式」──能夠欣賞花的人,便可以傾談政治,因為兩者都關於「判斷」的。第四章試圖將幾套理論架接起來回應佔領區藝術展現,既是關於香港處境,同時關於藝術,從中可以看出洪席耶的影響:究竟觀賞性 (spectatorship) 會否是存在一種游移的狀態?這並非純粹的盲動,而是有積極的能量讓你能跳出來反思現有框架,讓彼此看見彼此。最後我想提出幾個問題延伸討論。麗君談論pure gesture時用了舞蹈(紀錄者按:「與傘共舞」的部份)為媒介,而談論佔領區內出現的物品時又強調其超出工具性,你在這方面有沒有想再深入討論?與2019年又有沒有可比較性?
 盧建民「行山」攝影
盧建民「行山」攝影
問答環節
譚:麗君老師對講者的分享有無回應?
彭:暫時沒有。我反而想邀請譯者李祖喬作分享。
李:首先這部書很難翻譯,內裡的理論運用很龐大而複雜,需要許多協調。不過,作為一名香港研究者,讀到這本書時很興奮。因為我常常思考,研究香港應該如何與全球作對應?這本書很集中地與阿倫特對話,我自己最喜歡的是談論自由和城市權的部份。香港作為難民城市這個想法,在香港研究的認知中屬於基本認識,但是,如何將「難民城市」概念化、理論化來談論城市與政治,則可由麗君老師這本書轉入許多深入分析。例如從難民城市的視角來思考現時討論熱烈的民族主義、香港民族論,這種對邊境的界定、游移和出入,都可以深入對話。另外,我喜歡談論香港人最常提在口邊的「自由」,亦是西方世界、甚至中國認為香港作為城市最具力量的、主導的價值,但麗君要談卻是自由與城市內其他價值之間的張力與拉扯。例如她談及在一個單純地談論「自由」的狀態下,其實混和了許多Communist terrorism在其中,不能簡化成民族或者其他群體認同。我認為這種實與虛之間的討論是非常有趣。最後,我想把握機會提問:你寫法治的時候,究竟想傳遞怎樣的訊息?書中試圖從傳柯的生命政治轉換去談阿倫特提出的「生活政治」,似乎很想告訴大家要堅持法治精神,但另一方面又提醒我們可以主動改變法律。這是否在建議香港應該建立自己的法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的,例如由中央定立國安法這類外加的法規?
梁:我想追問,書名為《民現》,是民眾的現身,但整本書沒有正面回應《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這本書其實直至現在仍然是大家書寫香港時很喜歡引述的著作,同時亦受到不同學者試圖去拆解的概念。作為一位文化研究學者,麗君會如何回應這個概念?另外,我想向大家介紹2005年的攝影展《香港觀記》(Hong Kong Four-cast),內裡有一篇由田邁修 (Matthew Turner) 撰寫的導論building on appearance中回應,批評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的說法很華麗地使用了後殖民、文化研究的理論,可是這說法卻害人不淺。其實他運用了一種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來回應消失的政治,展覽舉行於七一之後,他很歡喜於看見人民在街頭現身、上街。我想問麗君是否也同樣希望處理這問題?
彭:我恰巧剛剛在《端》發表一篇短文,解釋了現身的民眾 (appearance demos) 為何意思。Wendy Brown曾經寫過Undoing the Demos一書,提到新自由主義具有很大的威力拆散民主,令人民解散回到個人的、私人的狀態。某程度上我想回應此說法,因為香港其實是頗為信仰新自由的城市,但是,我們並未被拆散,一樣對民主有概念與意識。其實我也有回應梁寶山剛才提到阿巴斯的說法。當群眾真正出現,大聲地表達自己的現身,我們便要處理消失這概念。其實阿巴斯這本在1997年出版的書提到消失與現身之間的曖昧與拉扯,認為兩者關係複雜。但現在不同,2014年及2019年間的群眾走上街頭,用盡一切力量表達自己的存在、出現,抗拒消失,某程度上與前論是兩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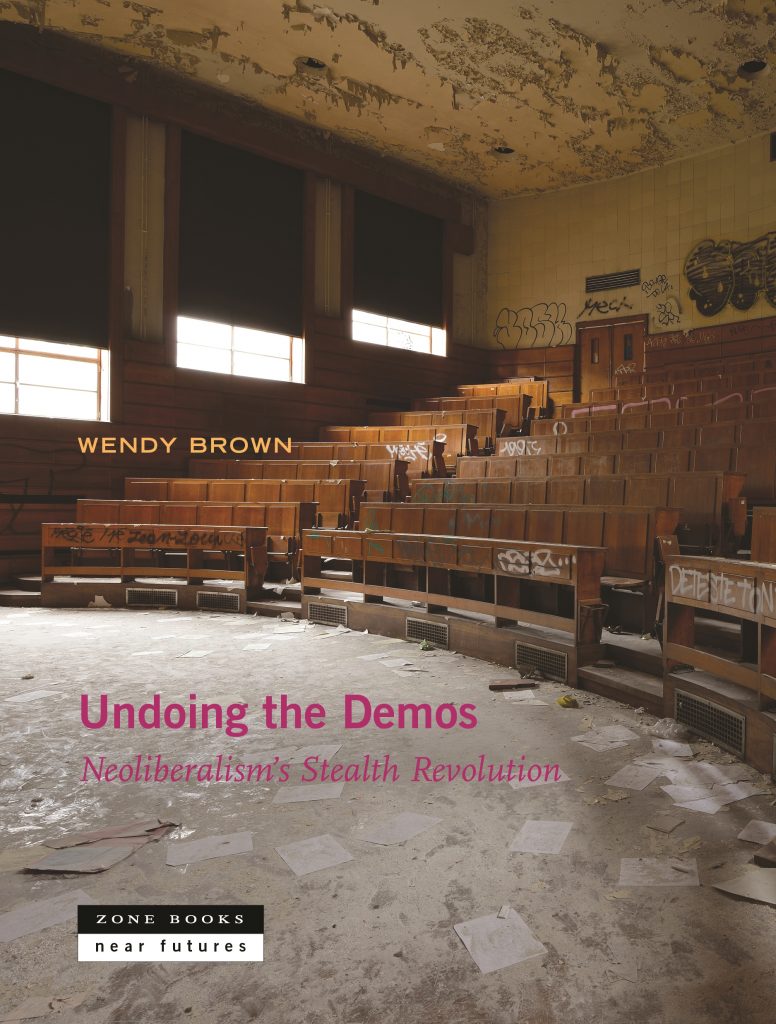
回應剛才李祖喬的提問。其實所有政權的核心可能都是暴力──亦即阿甘本所談及的例外狀態,認為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穩定、和平與繁榮是建基於建立「例外」、透過暴力來維持。從這方向來看,無論如何包裝,所有政權體系的核心都是暴力。反過來說,法律的核心,從理論層面來談,其實是不服從。這與我們平時認為法治就是服從法規不同。很多西方學者都提出,法律其實是由人、由社群來決定的,然後授權這套律法來治理我們,但最後的權力仍然在群眾的手裡。只有人民掌有不服從的選項,法治制度才可以進行,若不,這制度在現代社會之下終將崩潰。但同時,如果我們都不服從法律,法治也一樣不能成立。這一點是很矛盾的,怎樣才能在一套嚴謹的法律底下允許人民不服從法律?如何反映返人民才是法律的主人,但人民必須服膺於法律的權力?不得不認清的是,授權由一套法律來管治群眾時,亦代表群眾願意在法律面前先放下自我。而絕大部份的國家法律圍繞「公民抗命」的議題時,都是相當審慎和諸多掣肘,這不單是國家施行的,也是人民認同的,因為絕大部份人都不希望隨便「攬炒」。我想我們在香港天天都在問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能夠問就很好。
至於藝術的工具性,亦是眾多論者一直在討論的問題。我們認為藝術不是宣傳、也不是文宣。當藝術只等同文宣,便意味著藝術是盛載意識形態為目的工具。藝術是否需要比文宣多些自由地?所以我舉了pure gesture的例子,一種純粹的肢體舞蹈動作與空間的關係,你可以詮釋它,卻沒有一種說法可以完全解釋它。當這個藝術展現提供一個複雜的詮釋空間來抗拒一個簡單化的意義,都可以說藝術尋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空間。
聽眾A:黃色經濟圈是否一種共居 (cohabitation) 狀態?
彭:我認為是的。不過,假如圈中缺乏一個多元對話、不同的空間,可能又回到一種二元對立的、純粹的敵我關係之中。當然,二元的狀況現時是很逼切的議題,但是,在這狀況下如何思考一個群體內部的多元,又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聽眾B:城市權的達成需要與更上一級、掌有主權的政府討論權力分配。以香港現在的情況,「城市權」如何由上而下地提出、促成甚至確立?
彭:我認為現在這狀態很難與上層討論權力分配。眼下我們和你所說的那種上層架構之間已經失去信任基礎。我想這個狀態很不理想,但我們又希望盡做。我想可森談到的想法很好,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思考如何參與這個城市。我相信如果我們無法與他者溝通,或者仍然可以努力保存這城市的底蘊,例如建立我們的社群、公民社會。
聽眾C:我想延續剛才那位聽眾B關於「城市權」的提問,也想問問張可森的想法。我認為「城市權」是很吸引的概念。歷史中的香港,雖然有殖民宗主國,但頗長一段時間裡這位殖民主不太理會殖民地。這使香港成為一個半自治體,從歷史事實發展中可以參考出「城市權」的概念。這就涉及「多重主權」的狀況。其實這次疫情很能見出「主權」的不同層次。以美國為例,白宮與州政府的決定可以有不同,可見國家內部有不同層次的主權與權力。我想就兩點提問,一是城鄉差距,另外是城市與國家的關係。從美國或英國的大選為例,投票予政治取向較基進的政黨的大多為城市居民,投票給政治較保守的政黨的則多為鄉間居民。若我們暫不理會國家和城市的差距,先談論張可森所說的與他城締結姐妹城市的國際都市、麗君所提到的公平城市 (fairness city),其實是在於一種基進的基礎下思考的發展方向,是否忽略了各個城市與它們的鄉郊之間的差距?而城市又有另一個很關鍵的概念,城市是新自由主義集中的地方,以香港為例,我們和他城聯結的基礎價值是什麼?中環價值?這又與我們現在的訴求不同。另外,也是剛才聽眾的提問,城市有其自主權,但當國家不停希望收編這種自主權時,我們又應如何?剛才麗君回應了不少城市與國家的關係,我很想多聽聽各位講者對城鄉差距這種城市內部矛盾的看法。
 Credit:Studio Incendo
Credit:Studio Incendo
張:我亦曾問過麗君老師,會否對一國兩制太有信心。一方面,我很好開心這本書可以由香港的歷史經驗提煉到一些要素來改善全球狀況,但另一方面,我很遺憾於這本書的構想似乎無法應用於現時的香港。我很喜歡德勒茲談論「concept」作為一塊磚頭的概念,你可以選擇積存磚頭來建屋,也可以選擇把它投擲出去。而「城市權」這個概念可以投往何方,我很期待。關於城鄉差距,我自己亦思考許多。眼下的全球其實是由城市主導的發展,但香港又存在吊詭的地方,香港的鄉郊,其實就是新界,但這些年來亦有不少人努力地回頭保育香港這些鄉郊的部份。我想這是一個方向縮少城鄉差距。
彭:簡單回應。城鄉差距,我覺得香港當然有「鄉」,而「鄉」在香港甚至很有優勢。這與我們所想像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鄉」是很不同的。特別若我們談論的是香港原居民的某種權利,更加與外國情況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思考這種鄉村的優勢:什麼時候我們要回應香港特有的城鄉不公,鄉村又在何時與城市有政治上的交流與回應?香港的個案在全球城市之間是很特殊的。「中環價值」亦是這本書想問的問題。經過2019年,相信大家都開始關心「經濟邏輯」究竟與「政治邏輯」有多少共通、重疊與分別。中國主要以經濟邏輯來處理香港的政治問題,認為只要給予經濟上的發展與機會,讓香港變成上海,那麼現有的問題便會消失。中國看不見的是香港很核心的政治問題。最簡單,香港人談論「尊嚴」(dignity) ,用經濟邏輯是絕對無法解決的。同樣地,我們也不能不把經濟問題拉入政治問題來談論。現在許多全球左膠都批評香港反修例運動是一場資本主義者的運動,缺乏階級問題意識。這種說法當然有對香港運動不理解的地方,但他們有對階級問題的執著,我們也需要反思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概念發展,為香港製造了許多不平等的問題。
我又曾經與梁寶山談論過「共業」的問題。其實阿倫特與佛教可以溝通,她所談論的所謂自由的狀態,某程度上便是因緣的議題,由許多因所結成許多的果,人們要共同承擔這份「業」。阿倫特希望大家離開西方的、簡化的工具性思維,而佛家亦希望人不要簡單地覺得人與世界只屬一種予取予求的關係。現在讀論阿倫特可能是很「離地」的行為,但是,重要的是阿倫特經歷過集中營的生活,當她能夠站出來說不應把世界簡化成敵我關係,這是很值得大家參考的。
 Credit:qbix08
Credit:qbix08
張:我想補充一點,剛才提到法治的議題。書中提及「法」有兩組概念,一是希臘的nomos,一種是羅馬的lex,前者是先於政治的一套法規,後者則是較為開放的,談論立法的。為何大家現在認為法治已死?因為nomos已經壟斷,壓倒了走向lex的可行性。
梁:我想很快回應兩點。書中有提及intersubjectivity,如果以一種較為傳統的亞洲視角來思考,其實是建基在「空」,可以包含不同的詮釋。不過「空」是很大的議題,現在未必能細談。而intersubjectivity亦指涉另一個non-difference的議題,即是「無我相,眾生,壽者」,如果套回我們現在的討論,「空」就是允許一些論述呈現而不至同質化和本質化的空間。麗君提及希臘劇場對面具的運用,原意是防止演員將個人帶入舞台。但是,這個面具何時戴上和除下,則是大家自由自主地決定的。我不知道你寫到這一部份時,街頭的人們開始戴口罩的日常沒有。事實上,戴口罩不止於保護個人身份,同時代表我們進入公民角色,走入群體。
李:最後追問一個問題。這本書無論是寫作或翻譯的過程,香港似乎都處於示威中的狀況。在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寫評論或提出說法很容易「過時」,但學術著作似乎可以面對較長遠的時間。你提及自己在2016年間寫完呢本書,相信當時中央仍未有像今天的干預,你心中是否有這種對論述時效的想法,以致著述中呈現出相當的樂觀?另外,我們常常說香港是城市,想知道你心中有無其他城市與香港作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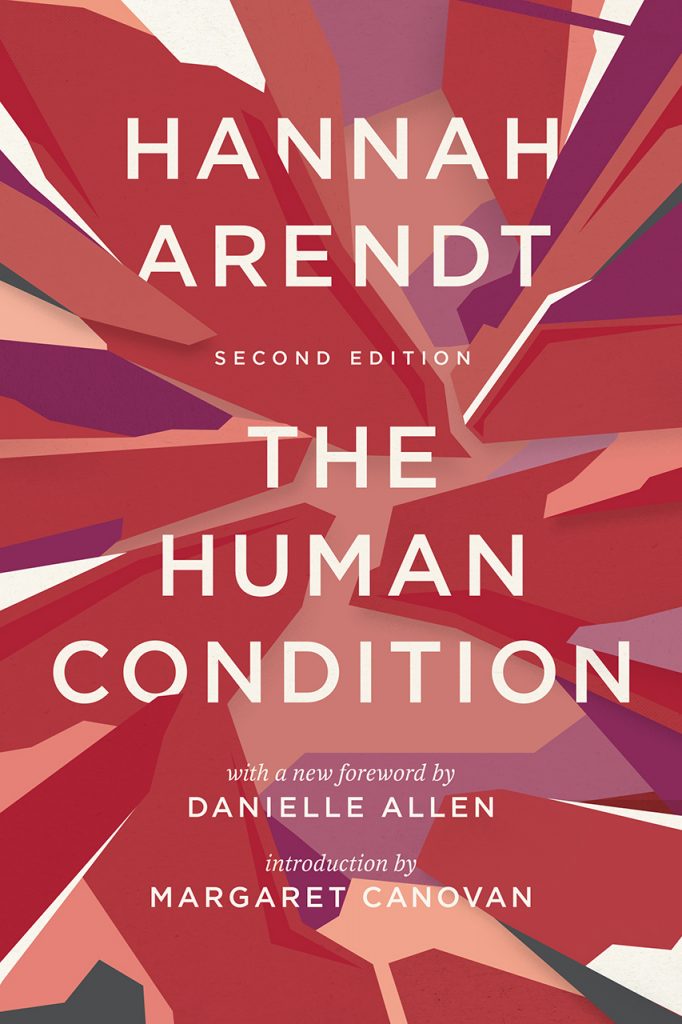
彭:阿倫特於1958年寫《人的條件》,之後幾十年大家開始忘記這本書,但在千禧年後,全世界突然又開始討論這本書。七、八十年代其實已經很少人再談論阿倫特。特別是,她的意識很反共,當時的左翼──包括女性主義者──都對她諸多批評。現在再談論她,大抵是因為大家開始意識到她思考的寬廣,不能被簡化的左右位置來定義,有人發現她提出的思考可以應世。我想我沒法與她的成就相比,但做學術的好處是,學術著作不容易被消費的市場所洗刷甚至改變,可以參與較長遠的討論。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城市。我在三藩市留學時,在當地居住一段長時間。三藩市人有很強烈的認同,會表示自己是「三藩市人」而不是「美國人」;又例如「紐約客」New Yorker的稱謂,許多城市的居民事實上對原生城市都保有一種特別的歸屬感,他們的身份認同,除了屬於國家,同時亦屬於城市。在這一點上,本書的立足點,是香港這個城市。
譚:時間差不多。很感謝麗君老師的現身說法,也多謝梁寶山和張可森的分享。作為出版商,當然不希望一本有份量的著作要等五十年後才有人討論。大家可以到序言、生活書店、榆林、開益等書店,或者在我們手民出版社的網頁購買此書。
(原載於別字第三十二期:https://zihua.org.hk/magazine/issue-32/article/the-appearing-demos-seminar/)
